枷是古代套在犯人脖子上的刑具。將犯人枷項后綁在衙門之前或鬧市之中示眾,又是一種殘酷的刑罰。
枷本來是一種農(nóng)具,又叫做柫或連枷,其樣式是在一根長竿的一端固定一節(jié)活動的短竿,人用手揮起長竿,帶動短竿,用來擊打堆在禾場上的稻谷。古代齊地所說道“耒耜枷芟”,指四種常用的農(nóng)具,枷為其中之一。現(xiàn)代在一些偏僻的鄉(xiāng)村里,仍然可以看到有些農(nóng)民使用這種原始的農(nóng)具打稻谷。由枷字的本意又引申為“擊打”的意思,如《后漢書·馬融傳》里的“枷天狗,紲墳羊”一句中,“枷”字即可解釋為“擊打”。
枷作為刑具,早在商、周之際就開始使用了。《周易·噬嗑》篇有“何校滅耳”一句,前人注解說:“校,枷也,罪重械其首也。”顯然,那時的“何校”(即“苛[疑為“荷”,通假字——骨頭注]校”)就是后來的枷項。除《周易》之外,枷項的做法最早見于《晉書·石勒載記》,其中寫道,東晉建威將軍閻粹慫恿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在山東捕捉北方的胡人賣給富家作奴隸,得到的錢財補充軍需。司馬騰就派部將郭陽、張隆等擄掠了不少胡人,把每兩名胡人用一面枷枷在一起,準備押送到冀州。后來成為后趙皇帝的石勒當(dāng)時才二十來歲,也在被枷者之列。這時的枷的式樣、大小、重量已難詳考,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種用木頭制作的固定俘虜脖項的刑具,二人一枷是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后來對枷逐漸改進并普遍采用,式樣也大體統(tǒng)一。南朝蕭子良《凈住子》云:“壁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可見,這時的枷已成為監(jiān)獄中管理囚犯的一種常備器械了。
北魏時,朝廷正式頒定枷為官方刑具之一,所以后世有人認為枷“始自后魏”。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枷的制作還不統(tǒng)一,當(dāng)時法官和州郡長官普遍制造重枷、大枷。除了用枷之外,還給犯人的脖子上掛石塊,綁石塊的繩子深深勒進皮肉里,甚至勒斷項椎骨。太和五年(481),魏孝文帝元宏下詔說,若不是犯下謀逆大罪且有真憑實據(jù)的犯人,不許用大枷。但什么才算是大枷,還沒有固定的標準。永平元年(508)七月,魏宣武帝元恪下詔讓尚書檢查各地所用的枷和杖的違制情況。尚書令高肇,尚書仆射清河王元懌,尚書邢巒、李平和尚書江陽王元繼等人,經(jīng)過調(diào)查,把有關(guān)情形及處理意見奏知宣武帝,經(jīng)圣旨批復(fù),規(guī)定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用來懲罰叛逆謀反者,各臺寺州郡原來制造的大枷都要焚毀,不許再用。這時規(guī)定的枷的尺寸雖然仍舊相當(dāng)大,但畢竟有了可以參考的統(tǒng)一標準。
就在魏宣武帝下詔之后,還發(fā)生一件有趣的事。宋翻任河陰縣令時,縣衙里原來存放著一面大枷,名叫“彌尾青”。有人說,朝廷下詔不讓用大枷了,這面枷就燒掉吧。宋翻說:“不要燒,暫且把它放在墻根下,以待豪滑之徒。”不久,有個名叫楊小駒的太監(jiān)到縣里辦公事,頤指氣使,,十分驕橫,宋翻就命令衙役取來“彌尾青”給他戴上。楊小駒受了一場惡氣,回到宮里向宣武帝哭訴,宣武帝認為是打狗欺主,勃然動怒,傳旨讓河南府尹審問宋翻,同時下詔說,宋翻違抗先帝的旨意,使用超重大枷,是擅行威權(quán)以沽名釣譽。宋翻上書申辯說:“這面枷不是我制作的,之所以留下它,不是為了懲罰百姓,而是要懲治楊小駒這樣的兇暴之徒”。這件事說明,魏宣武帝以前確實到處有大枷,宋翻不畏權(quán)貴,敢于對抗有特殊身份的太監(jiān),他的勇氣和魄力令人贊賞,因此一舉而名震京師。
從北齊、北周到隋,都沿襲北魏的法規(guī),普遍用枷。《齊律》規(guī)定:“罪行年者鎖,無鎖以枷。”《周大律》規(guī)定:“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這都說明枷在這時是不可缺少的刑具。隋開皇年間,朝廷也曾對枷和杖的大小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
唐代用枷更是常事。《唐六典》載:“諸流、徒罪及作者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一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頭三寸以上,四寸以下。”但是,唐代的一些酷吏并不按照規(guī)定的尺寸,而是挖空心思地制作大枷、重枷。武則天時,著名的酷吏來俊臣制作的枷最為出名.其所制作的大枷有十種名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還有一種特重的枷名叫“尾”。從這些名目可以想見,每一種枷都是十分厲害,令人難以承受的。與來俊臣同時的另一名酷吏索元禮手段更加奇特。他讓犯人跪在地上,雙手奉枷,在面前的枷板上再放一摞磚,這叫做“仙人獻果”。或者讓犯人站在高處的橫木上,把他的項上的枷掉轉(zhuǎn)方向,使長的一端朝后,犯人必然身體要前傾,而脖子也就被勒得更緊,這叫做“玉女登梯”。索元禮用這樣的種種手段,常常把人折磨致死。
宋代,對枷的重量有一定的限制。開始規(guī)定,枷分二十五斤和二十八斤兩個等級。景德初年,提點河北路刑獄陳綱上書請制杖罪,并且提議增設(shè)十五斤重的枷為三等。宋真宗趙恒準奏,下詔頒布施行。但在實行的時候,枷的重量常常超出規(guī)定。有的地方制的枷用鐵皮包邊鑲角,稱為“鐵葉枷”,如小說《水滸傳》中林沖和武松發(fā)配時戴的枷就是七斤半重的“團頭鐵葉護身枷”。有的地方用鐵鑄成鐵枷,其重量當(dāng)然要遠遠超過木枷。盡管在宋太平興國三年(978)曾頒發(fā)過不得以鐵為枷的詔令,鐵枷仍被某些酷吏使用。金代的枷常常超出規(guī)定,泰和四年(1204)七月,金章宗完顏璟曾派官員到各地巡視,對濫用重枷的現(xiàn)象予以查究,但并不能徹底禁絕。
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詔令統(tǒng)一枷的型號。規(guī)定枷長五尺五寸,兩端寬一尺五寸,用干木制作,死刑犯人戴的枷重三十五斤,徒罪、流罪犯人戴的枷重二十斤,杖罪犯人戴的枷重十五斤,長短輕重的數(shù)據(jù)都刻在枷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詔令,凡在京的各衙門所用的刑具都必須經(jīng)過檢查,符合規(guī)定的標準才準許使用。而且,各種刑具必須由指定的地方制作,不得隨意制造使用。如規(guī)定由應(yīng)天府采辦笞杖、訊杖等杖具,龍江提舉司成造枷樞,寶源局打造鐵索鐵鐐等。但是,實際上明代用枷超重的情況比以前各代更厲害,由宦官控制的東廠、西廠和錦衣衛(wèi)的大小爪牙們嗜血成性、殺人如草,他們用的枷越做越重、越做越奇。
英宗正統(tǒng)年間,國子監(jiān)祭酒李時勉得罪了宦官王振,王振以砍伐文廟前古木為大不敬的罪名,制作了幾面百斤大枷,命令將李時勉和司業(yè)趙琬、掌饌金鑒三人枷號示眾。其中一面枷重一百多斤,是王振讓人為李時勉特制的,金鑒說:“我年輕力壯,給我戴這面枷爸。”李時勉說:“老夫筋骨更堅,還是我來吧。”就搶先戴了重枷。當(dāng)時正是炎夏盛暑天氣,他們被枷號三天仍未解除,于是激起了公憤,監(jiān)生李貴等千余人到皇宮門前請命。有個叫石大用的監(jiān)生愿意以自身代替李時勉戴枷示眾,其他監(jiān)生都一齊呼喊號叫,聲音傳到內(nèi)廷。皇太后(宣宗孫皇后)聞知,急忙責(zé)成英宗立即釋放了李時勉等人。
正德初年,宦官劉瑾專權(quán)時制作的大枷重達一百五十斤。給事中安奎和御史張彧奉旨到外地盤查錢糧回京,劉瑾向他們索賄而未能滿足,就尋借口把安、張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枷號于東西公生門。當(dāng)時是夏季,大雨晝夜不停,二人淋得像落湯雞似的,也沒有人敢將他們移動一步。都御史劉孟赴任延遲了日期,被逮至京師,枷號于吏部衙門外。御史王時中也因得罪劉瑾,被枷號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圍觀的群眾都忍不住流淚,文官們遠遠地望見這種景象,都垂頭喪氣,沒有一個人敢走到跟前看一看。此外被枷號的還有給事中吉時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浚,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吳獻臣因為彈劾劉瑾,被枷號于午門前長達一月之久,反對劉瑾的官員被枷死的說不清有多少人,平民百姓因小罪被枷死的就更多了。
因為正德年間的枷號的做法過于殘酷,明世宗朱厚驄即位時不得不作些糾正。嘉靖元年(1522),世宗詔令兩京法司和錦衣衛(wèi),在天氣炎熱時對該枷號示眾的囚犯要暫免枷號,以顯示圣上惻隱之心。但過了不久,又變本加厲地恢復(fù)正德時的舊規(guī)。有個叫劉東山的人,告皇親張延齡兄弟謀反,錦衣衛(wèi)指揮王佐竭力為張氏辨冤,反過來指控劉東山為誣告,于是將劉東山用大枷枷號示眾三個月,然后充軍戍邊。劉東山受盡摧殘,死于戍所。這是見于記載的明代對犯人枷號時間最長的一次。劉東山能堅持到底,還算得上是硬漢子,嘉靖年間有不少人枷號的時間為一個月或兩個月,結(jié)果期限未滿就戴枷而死。
萬歷年間,明神宗朱翊鈞又制造一種新式刑具,名叫立枷。這種枷前面長,后面短,長的一端觸地,犯人被枷住脖子,身體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東廠和錦衣衛(wèi)對皇帝欽定的案犯,常常要用立枷,犯人大多在一天之內(nèi)就送了命。如果有不能很快即死的,監(jiān)刑的校尉就把枷銼低三寸,這樣,犯人就站不直,只能稍微彎曲著雙腿,勉強支撐,不一會就力量用盡,氣絕身亡。如果犯人不是廠衛(wèi)注意的重要案犯,或者在沒有仇家監(jiān)督的情況下,犯人的家屬就花錢雇傭乞丐,讓乞丐夜間用背扛著受刑者的臀部,讓他半坐在乞丐身上,這樣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腳力,不致于速死。還有人說,受刑者每天生吃一只貓,可以提精神,抗折磨,不知是否真的有效。被立枷枷死的人不可勝數(shù),大多是因為得罪了廠衛(wèi)的頭目,而被用這種方法害死,只有萬歷二十年(1592)樂新爐、諸重光是因為奏事不實,觸怒了萬歷皇帝朱翊鈞,于是皇帝親自下令,讓東廠把樂、諸二人用立枷處死。當(dāng)時還有一個規(guī)矩,受刑者如果在不滿應(yīng)該枷號的期限內(nèi)死去,監(jiān)刑者不準家屬提前收尸,只是把他的尸體就地用土掩蓋一下,必須等到了期限,監(jiān)刑者向上司回報之后,才準許將尸體運走安葬。如果是夏天,到安葬時,尸體的血肉已經(jīng)腐爛凈盡,只剩下一具骷髏了。所以,萬歷時的士大夫們談立枷則色變,認為它的殘酷性超過大辟。天啟時,魏忠賢主持東廠,也愛用立枷,先后枷死六七十人。明毅宗朱由檢即位時,聽說立枷特別殘酷,就問左右這立枷是干什么用的,太監(jiān)王體乾回答說,是用來懲治巨奸大惡的。毅宗說:“雖然那樣的人應(yīng)該懲辦,但他們受這樣的刑罰也太可憐了。”據(jù)說,當(dāng)時魏忠賢在旁邊聽了毅宗的這句話之后,嚇得直縮脖子。不久,毅宗除掉了魏忠賢,直到明朝亡國,再也沒有使用立枷。
清代仍有枷項之刑和枷號示眾的做法。康熙八年(1669)規(guī)定應(yīng)該枷號的犯人所戴的枷重的七十斤,輕的六十斤,長三尺,寬二尺九寸,詔令內(nèi)外問刑衙門,都要按刑部制作的式樣執(zhí)行,不得違例。各地的官員雖然大多能遵守規(guī)定,但有個別的酷吏又獨出心裁,變化枷的花樣。長洲縣令彭某設(shè)立紙枷,就是用薄紙做成枷的摸樣,他同時還制作了“紙半臂”,就是紙做的背心。對欠糧的人,彭某就命令給他戴上紙枷,穿上紙半臂,縛在衙門前示眾。這種紙刑具雖然很輕,但彭某規(guī)定一點兒也不許損壞,否則要用其他酷刑嚴加處治。戴“枷”者必須終日呆站,紋絲不動,這種被約束的痛苦,比戴真正的木枷還難以忍受。古時的紙又薄又脆,紙枷和紙半臂都很難完好無損,因此被枷者常常在剛戴不一會兒就把它弄破了,于是接著被施以酷刑。當(dāng)時,長洲百姓對這種做法十分痛恨,有個無名文士曾寫詩一首,貼在縣衙墻上,詩云:
長邑低區(qū)多瘠田,
經(jīng)催糧長役紛然,
紙枷扯作白蝴蝶,
布褲染成紅杜鵑,
日落生員敲凳上,
夜歸皂隸鬧門前。
人生有產(chǎn)須當(dāng)賣,
一粒何曾到口邊?
詩中第三四句寫戴紙枷的人一不小心就會把紙枷扯碎,紙片飄飛,像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但這樣一來就難免受到重杖或夾棍的責(zé)罰,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把布褲染紅。全詩傾訴了長洲百姓被逼交官糧而遭受刑責(zé)的痛苦,反映了古代吏治的殘暴。從此詩可以看出,紙枷的殘酷并不在紙枷本身,而在于附加的苛刻條件。彭某的暴行,激起了長洲百姓的強烈反對,從來,朝廷不得不把彭某罷官勘問,彭某不久便死于蘇州花橋巷寓所。
古代的枷項之刑,一般來說主要施用于男性犯人,而對于女犯則用械。械是用硬木制作的,長一尺五寸,寬四寸左右,中間鑿兩個小孔套在女犯人的小臂上,固定住兩只手,相當(dāng)于金屬的銬的作用。但有時對女犯也用枷。明代有一位女子因通奸罪被官府拘拿審問。某郡守聽說這女子很會作詩詞,就取出械給她看,讓她以械為題作一首詞,并且說,如果詞作得好就赦免她。這女子略思片刻,賦《黃鶯兒》一首云:
奴命木星臨,霎時間上下分。松杉裁就為圓領(lǐng),交頸怎生,畫眉不成,眼睛兒盼不見弓鞋影。為多情,風(fēng)流太守,特贈與佳人。
細觀詞意,這女子所詠的不是械,而是枷。“木星臨”,指枷是用木頭制作;“上下分”,指枷是由兩塊木板組成。“圓領(lǐng)”一詞,顯然指套在脖頸上。戴著枷,自然不能“交頸”而眼,而且手無法畫眉,眼睛看不見鞋尖。詞的末句“特贈與佳人”五字,有的書中作“獨桌宴紅裙”,既然比作飯桌,肯定是指枷無疑。這位女子不愧以文才知名,她把作為刑具的枷加以詩化和藝術(shù)化了,描繪得那么形象、生動,同時表現(xiàn)出作者內(nèi)心的坦然和性情的幽默感。那位郡守贊賞女子才思敏捷,就沒有判她的罪,把她釋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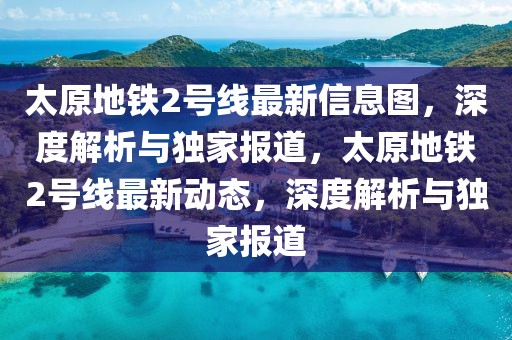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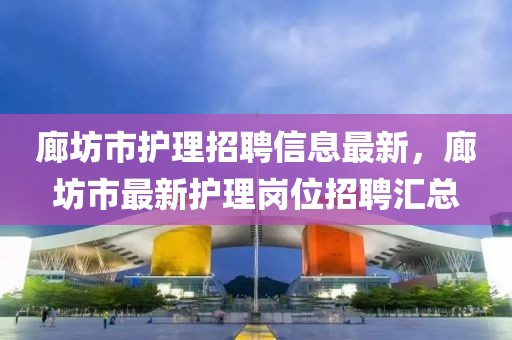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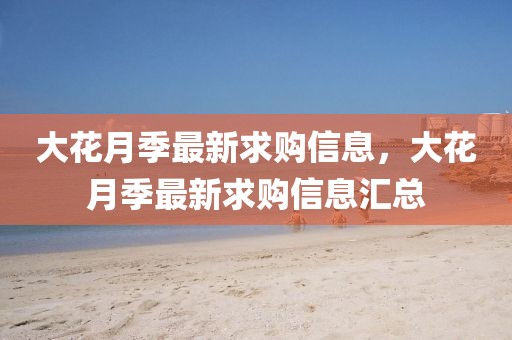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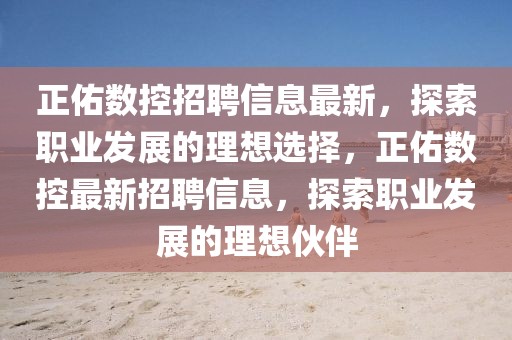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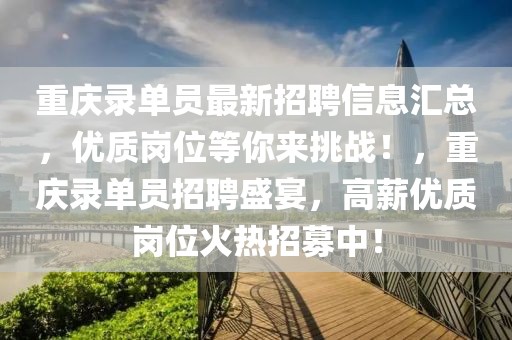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