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不列顛尼亞"》
新華社記者 周樹春、楊國強、徐興堂、胥曉婷 、 周婷、楊興
在香港飄揚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米字旗最后一次在這里降落后,接載查爾斯王子和離任港督彭定康回國的英國皇家游輪"不列顛尼亞"號駛離維多利亞港灣--這是英國撤離香港的最后時刻。
30日下午在港島半山上的港督府拉開序幕的。在蒙蒙細雨中,末任港督告別了這個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
4點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視著港督旗幟在"日落余音"的號角聲中降下旗桿。
根據傳統,每一位港督離任時,都舉行降旗儀式。但這一次不同:永遠都不會再有港督旗幟從這里升起了。4時40分,代表英國女王統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帶有皇家標記的黑色"勞斯萊斯",最后一次離開了港督府。
掩映在綠樹叢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個半世紀中,包括彭定康在內的許多港督曾對其進行過大規模改建、擴建和裝修。隨著末代港督的離去,這座古典風格的白色建筑成為歷史的陳跡。
晚6時15分,象征英國管治結束的告別儀式在距離駐港英軍總部不遠的添馬艦軍營東面舉行。停泊在港灣中的皇家游輪"不列顛尼亞"號和臨近大廈上懸掛的巨幅紫荊花圖案,恰好構成這個"日落儀式"的背景。
此時,雨越下越大。查爾斯王子在雨中宣讀英國女王贈言說:"英國國旗就要降下,中國國旗將飄揚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管治即將告終。"
7點45分,廣場上燈火漸暗,開始了當天港島上的第二次降旗儀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個叫愛德華·貝爾徹的英國艦長帶領士兵占領了港島,在這里升起了英國國旗;今天,另一名英國海軍士兵在"威爾士親王"軍營旁的這個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當然,最為世人矚目的是子夜時分中英香港交接儀式上的易幟。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鐘,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國對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統治宣告終結。
在新的一天來臨的第一分鐘,五星紅旗伴著《義勇軍進行曲》冉冉升起,中國從此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與此同時,五星紅旗在英軍添馬艦營區升起,兩分鐘前,"威爾士親王"軍營移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開始接管香港防務。
0時40分,剛剛參加了交接儀式的查爾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顛尼亞"號的甲板。在英國軍艦"漆咸"號及懸掛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的香港水警汽艇護衛下,將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顛尼亞"號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從1841年1月26日英國遠征軍第一次將米字旗插上海島,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一共過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個月零四天。大英帝國從海上來,又從海上去。
( PS :《別了,“不列顛尼亞”》選自《通訊名作100篇》(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 原稿署名為周婷、楊興,作者實際是四人:周樹春、楊國強、徐興唐、胥曉婷。發表時用周婷、楊興二人署名,在這里我們將作者署名為——周樹春、楊國強、徐興堂、胥曉婷 、 周婷、楊興共計6人)
一、 不落俗套,找準新聞視點和切入角度
我們知道其實很多主旋律報道,多數報道均秉持著提煉材料,形而上的空泛宣傳寫作手法,新聞事實服務于既定材料和觀點,注重整體全面,但是缺乏具體形象,以往的很多宣傳性報道以抒情言志為主,感情色彩濃烈。
這篇文章,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不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文章相當克制冷靜,力求“再現”事實,以保持新聞報道“客觀公正”的立場來呈現重大歷史時刻,寫這篇稿件的四名新華社記者以主觀情感深藏報道之外,通過精心選取的視角、素材選擇和戲劇性細節展現并記錄香港回歸重大歷史時刻,耐看耐讀,令人回味悠長,百看不厭。
現場時間為經,歷史時間為緯, 這篇文章立意高,內容新,角度和視點,獨樹一幟。對于正面報道,特別是人所共知的題材,要想稿件不落俗套,須通觀全局、提升站位,寫出新意與高度。《別了,不列顛尼亞》立意深遠,別具匠心,通過對新聞現場場景、過程、人物行為的精細描述,將讀者帶入現場,再通過氣氛烘托、拉伸時空距離等方式,營造出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歷史回響。
在當時的高度競爭的時效下,要寫出好作品談何容易?要出新意就不能照抄大量素材,就不能想著應付交差,這篇報道謀篇布局,策劃創意,著重讓報道見人見事,挖掘現場背后的歷史性瞬間和背后的厚重意義,現在即使過去了22年,仍然少有人能超越,有人甚至評價——這篇新聞作品是近30年以來,最為經典的一篇時政報道新聞特寫作品。
二、敘事結構:精巧別致,有章法
這篇新聞作品的題材是一篇新聞特寫,特寫也稱新聞速寫、新聞素描,要求用“特寫鏡頭”反映事實,實際上是一篇希望消息,新華社記者在香港回歸的重大歷史時刻,深入新聞事件現場,生動、形象地將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再現在讀者面前。
從謀篇布局來說,相當精巧別致,有章法。這篇新聞特寫消息一共11個段落:導語(第1段)、主體(第2—10段)、結語(第11段)。
(1)標題 ——別了,不列顛尼亞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回國、美國政府的白皮書發表之時,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別了,司徒雷登》。
這篇新聞作品活用此題,從字面上看,參加完交接儀式的查爾斯王子和末任港督彭定康乘坐英國皇家游輪“不列顛尼亞”號離開香港,消失在茫茫的南海夜幕中,這是現實的場景。另一方面,“不列顛尼亞”號的離去,象征著英國殖民地統治在香港的終結,中華民族的一段恥辱終告洗刷。實境是永別,虛境是回歸和雪恥。標題寓虛境于實境,獨具匠心又不留痕跡,絕對的好題!
《別了,“不列顛尼亞”》以此為典,仿擬為題,亦饒意趣,意味深長,潛在而實在地激發了讀者的民族自信與自豪感!
(2) 導語——(第1段)消息的第一自然段,或開頭的一兩句話,一般稱為導語。
第1段概述英國撤離香港的最后一刻,英國米字旗最后一次降落,接載英國王子和港督的游輪離開香港。
(3)主體——(第2—10段)導語之后,構成消息內容的主要部分。
主體部分共9個自然段,分四層, 主體部分集中描寫英國撤離香港那天的四個場景, 三次降旗(時間順序)。
(a) 第一層(第1~3段),場景1:港督府告別儀式(第一次降旗)。
港督府告別儀式是英國告別儀式的序幕,地點:港島半山上的港督府。時間:4∶30分,降旗。4∶40分,港督彭定康離開港督府。
(b) 第二層(第4~6段),場景2:添馬艦東廣場告別儀式(第二次降旗)。
添馬艦東面廣場的告別儀式,象征著英國長達156年統治的結束。
時間:晚6時15分,儀式開始。7時45分,降旗。
(c) 第三層(第7~8段),場景3:交接儀式(降旗與升旗)。
中英香港交接儀式是整個儀式的高潮。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時間: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鐘和7月1日的第一分鐘。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與此同時,添馬艦東廣場升起五星紅旗,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香港防務。
(d) 第四層(第9段),場景4:"不列顛尼亞"號離港。
時間:零點40分,查爾斯王子和離任總督彭定康乘坐"不列顛尼亞"號離港。
(4) 結語——(最后一段)消結尾響亮、有力,發人深思,給人啟迪。
用概括的語言敘述英國在香港統治的開始與結束。
三、現場感強:以眼睛為攝像機,以耳朵為錄音機
這篇新聞特寫作品在新聞的視覺化表達,情景真實性以及新聞受眾者感官體驗度方面堪稱經典。一句話,好的記者可以通過可視畫面,讓你身臨其境。
這篇文章的寫作者,多名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發生的現場,以眼睛為“攝像機”,以耳朵為“錄音機”,簡筆勾勒出的清晰可視的一個個場景、一幅幅畫面,讓你腦海里好像放電影一樣,一幅幅畫面,圖景還原回現場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1)以眼睛為攝像機
在現場目擊中,新華社記者以敏銳的觀察能力,在采訪現場捕捉到了精彩的鏡頭、典型的場面,并給予形象再現。
如文中寫的:“在蒙蒙細雨中,末任港督告別了這個曾居住過25任港督的庭院”,“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視著港督旗幟在‘日落余音’的號角聲中降下旗桿”,“停泊在港灣中的皇家游輪‘不列顛尼亞’號和鄰近大廈上懸掛的巨幅紫荊花圖案,恰好構成這個‘日落儀式’的背景”,“五星紅旗在英軍添馬艦營區升起”,“查爾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顛尼亞’號的甲板,在英國軍艦‘漆咸’號及懸掛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的香港水警汽艇護衛下,將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顛尼亞’號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這些場景描寫,筆法細膩,視覺呈現感強大。
記者還特別注意到以色彩“視覺效果”:黑色的“勞斯萊斯”、白色的總督府、綠色的樹叢,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這些簡潔的白描筆法,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個場景,一幅幅畫面,使新聞具有清晰的可視性。
(2)以耳朵為錄音機
不僅描摹了現場畫面,新華社記者在采寫中還以耳朵為錄音機,向大家傳遞了現場聲音,可以說這篇文章絕了,不僅讓你看見,還讓你聽見現場的聲音。比如文中寫到:“彭定康注視著港督旗幟在‘日落余音’的號角聲中降下旗桿”,“雨越下越大。查爾斯王子在雨中宣讀英國女王贈言”,“五星紅旗伴著《義勇軍進行曲》冉冉升起”,等等。這些描述,好像親臨新聞事實發生的現場,聽到降旗聲、下雨聲,講話聲和升旗的樂曲聲……從而受到強烈感染。
在《別了,不列顛尼亞》這篇新聞作品中,這些富有重大歷史儀式感的敘述,寫法是白描手法,勾勒畫面很簡潔,但都有著重大而富有內涵的歷史的意義,堪稱決定性的瞬間記錄,四名新華社記者通過自己的文字描述,讓讀者看到了一部有聲有色的歷史影像,它有情感,有故事,而且真實可信,不僅用眼睛觀察,而且要動用全身的感官去感知。
四、 抓住象征意義的典型性細節——聚焦含有深意的3次降旗與1次升旗
這篇特寫消息,著重描述了3次降旗與1次升旗,布局精巧,在當年有關于香港回歸的眾多報道中,這一篇報道算得上是“最別致有韻味的一篇”,要知道當年當時在現場有全球770多家新聞機構8400多名新聞記者,在報道這一重大事件,這篇報道能從千軍萬馬,雪片般的海量稿件中脫穎而出,確實是有獨到之處的。
為什么要著重聚焦國旗呢?這是因為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征與標志,英國米字旗的降下,象征著英國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的結束,五星紅旗的升起則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五、背景材料:用的巧,用的妙,用活了
懂新聞寫作的人都知道,新聞背景材料用不好是累贅,啰嗦冗長,無用,用好了那絕對可以把文章的縱深感,提高一大截子。事實上盡管每一篇新聞,不一定都要寫背景,但是,一篇好新聞其背景材料絕對是它的加分項。
所謂文以載道,人們讀一篇新聞,總是渴望明了這則新聞的背后意義。一般情況之下,新聞記者總希望將這則新聞的社會價值,能夠明確地傳達給讀者。但是,有很多時候因為記者不會用背景材料,讀者讀了文章之后,并不覺得有多么背景材料有什么重要性,甚至懷疑記者寫的是廢話,沒有必要性。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很多記者不善于恰當地運用背景材料,甚至根本不會用背景材料。
新華社名篇《別了,不列顛尼亞》巧妙地在文中穿插新聞背景材料,不僅會用,而且用的巧,用的妙,用活了!如提到彭定康離開港督府,就引入一些關于港督府歷史的背景材料,使得現實的場景有歷史縱深感,讓人更加體會出儀式本身的現實內涵。
這樣我們得到這樣一個啟示:
1.背景材料不能過長。背景材料用的過多,就會使得新聞淹沒在舊聞之中。在新聞中,背景材料畢竟不是主體,應寫得簡練些。
2.背景材料不能和新聞主題兩張皮。背景材料要與新聞主體有實質性聯系,要與新聞事實融為一體,形成有機的結合。在寫作中,“兩張皮”的背景材料是累贅,水乳交融的背景材料才是極品。
3.新聞背景材料用好了,可以變陳舊成新穎, 化腐朽為神奇,《別了,不列顛尼亞》的背景材料,用的巧,用的妙,用活了,正是由于有背景材料的襯托,這篇新聞作品的新聞價值才得以凸顯。
4.新聞背景材料要會用,要沙里淘金精選擇,化整為零巧穿插,新舊搭配妙轉換,這篇文章馬上就活了,和新聞主體緊緊融為一體,使人絲毫感受不到背景材料的拖沓與累贅!
六、結尾最后一句堪稱金句
這篇新聞作品,最難以忘懷的是最后一句,也是全文蘊蓄最深的精彩:“大英帝國從海上來,又從海上去。”
英軍從海上來到香港,最后又乘船從海上離開。從海上來,標志著英國開始了對香港的侵占,從海上去,意味著結束了對香港的殖民統治。
這最后一個句子,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來去二字,語意簡明,帝國去矣!寥寥幾筆,速寫歷史,意指興衰。從海上來,又從海上去,這里面一個“又”字深沉,意喻歷史正義的實現和百年國恥的洗刷。
新聞敘事彰顯深度力量,邏輯深度、歷史深度和情感深度融為一體,真高手也!
22年前的香港,中英易幟,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這是一個永載史冊的瞬間。這則堪稱經典的新聞作品,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盛事為載體,生動形象地記錄了英國王儲查爾斯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乘坐“不列顛尼亞”號皇家游輪撤離香港的最后時刻。
《別了,不列顛尼亞》表達了只有國家強大了、民族昌盛了,我們的民族和人民,才不會被人欺辱!表達了香港從古至今都是我們神圣國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激發了偉大愛國情懷,提升了民族自豪感,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可圈可點的名篇佳作,值得大家認真學習!
(本文作者為南方傳媒書院創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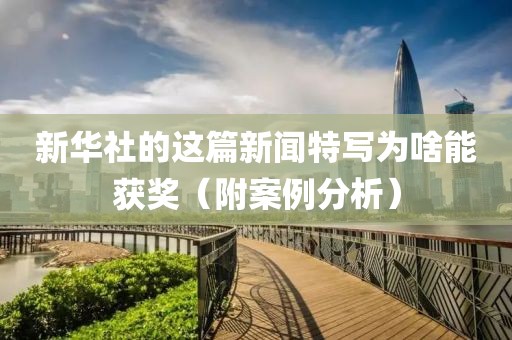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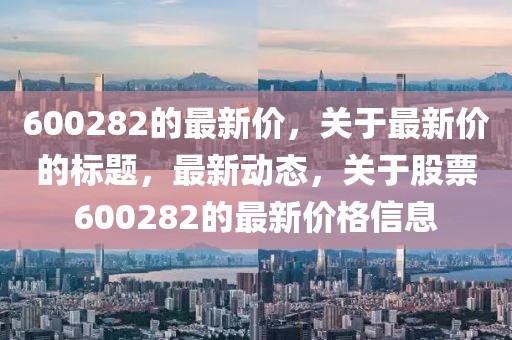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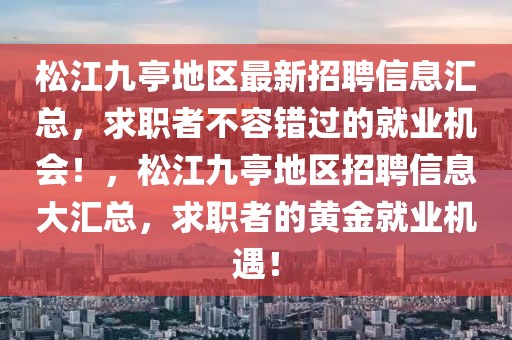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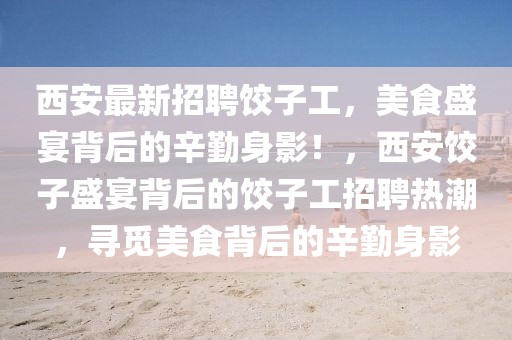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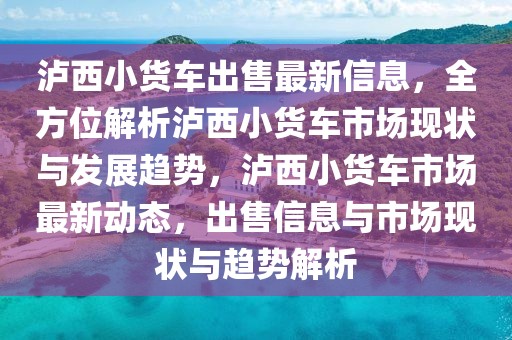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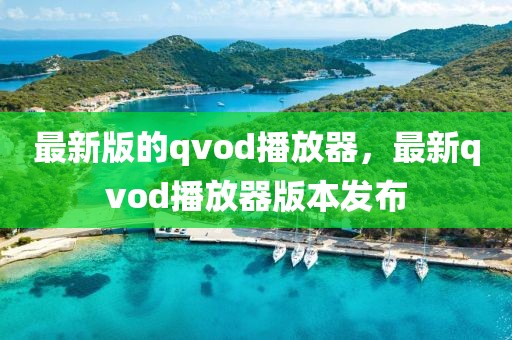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