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者如陶喆,從不抱怨環境,哪怕是像在金曲獎這樣的頒獎典禮的舞臺上,只要陶喆想,也能濃墨重彩地抽象一把。
在參加第28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時,陶喆說話一度被消音,換了3次麥克風都無效。第二年,他就自備了11支麥克風去參加頒獎典禮。他出場時,臺上放了5支立麥、4個迷你麥,2個擴音喇叭,還讓兩個工作人員扛著長桿收音器收音。
舞臺都沒有?沒關系,陶喆在哪兒拿起話筒,哪兒就可以是舞臺。
今年5月,陶喆在上海就辦了一場“全球首例行走的演唱會”。實際情況是,他當時是去同濟大學錄制節目,身穿休閑范十足的白色短袖衛衣,姿態隨意地拿著話筒邊走邊唱。絲滑的走位,熱情的互動,從學校大門一路唱到食堂,愣是把節目錄制現場玩出了演唱會的質感。
大多數被抽象文化認證和收編的公眾人物,往往緣起于網友的考古。像陶喆這樣,往事算開采中的資源庫,有新聞就算進貨的,可謂是獨一份。
“你是來害我的還是來幫我的?”這是胡彥斌走下第三季《我是歌手》決賽舞臺后,對陶喆說的第一句話。
原本是作為胡彥斌幫唱嘉賓登臺的陶喆,全程隨性發揮,硬生生地拉著胡彥斌一起貢獻了“陶胡想哭”的名場面。胡彥斌在之后接受采訪時,說陶喆屬于“人來瘋”,“喆學”中的無數個教材也應證了這一點。
當導師,隨口模仿學員發聲方式留下名作《天天嘴巴里含鹵蛋》;還是當導師,用一串“誒誒誒誒”開場示范轉音;早期參加臺綜,上演頂胯版《望春風》;在采訪節目里,說完“車如女人”的言論后,就地自主地演起了屏幕前觀眾的反應,被網友戲稱為“隨地大小演”;喝完酒后當街親狗仔;醉酒后找不到家,到警局待了一個小時;在自己的婚禮現場激動到飆高音,飆到破音。
在參加節目《最美和聲》時,更是貢獻了抽象版的《無地自容》。節目里,眾人合唱之余,韓紅把麥轉向了陶喆。隨即,陶喆在緊湊的鼓點里,即興來了一段堪比《忐忑》的歌詞演繹。
不過,陶喆也有棋逢對手的時候。
幾年前,陶喆和陳奕迅同臺合唱了彼此的經典曲目《飛機場的十點半》《兄妹》,但在那個晚上之后,這兩首都有了新名字——《垃圾場的十點半》和《兄貴》。仿若是老熟人之間才會有的默契,現場兩人一起走音,一起破音,一起爭著唱和聲。
到了《垃圾場的10.30》唱不動副歌的陳奕迅,在陶喆那句“是不是擁有以后就開始要失去”接了句“你說得對”,直接把難唱的部分又拋給陶喆。
這么多年來,陶喆之所以可以抽象而不自知,一路登上抽象之神的高位,依靠的就是一份超強自洽力。
多年后,陶喆自己坐在屏幕前觀看那場幫唱時,一開始還在淡定地開玩笑說胡彥斌兩條腿粗細不一。看到“讓我哭”的片段時,他自己也驚訝地問了一句“我在干嘛”,最后自我總結:“有一些演出你是要忘記的。”
如果說音樂,是陶喆的主場,那么他早期的MV,就是“喆學”的教學現場。
入行三十年有余,陶喆總共發行了七張錄音室專輯,幾乎每張都名利雙收。從黃專到藍專,再到《黑色柳丁》,陶喆只用了三張專輯就掙來了“教父”之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三張專輯間隔的時間分別為兩年和三年之久。
在做音樂這件事上,陶喆永遠是對自己最苛刻的那個人。在記錄了《黑色柳丁》制作過程的紀錄片《11號產房》的鏡頭里,他幾乎住在了錄音室里,工作臺的柜子里裝的是滿滿幾抽屜的、被他稱為“寶貝”的各種曲風、年代的 CD。當時才三十幾歲的他,一邊自嘲周末大家都出去玩了,自己在錄音室里做歌,一邊感嘆自己追不上時間。甚至會因為寫不出適合的 Pre-Chorus,毅然決然地將一首即將完成的歌曲直接從專輯里刪了。
這也是為什么陶喆的音樂作品是被無數個音樂學子用來逐拍逐軌學習,但陶喆早期的MV 卻是被用來逐幀逐畫截圖做表情包的。在早年的采訪里,陶喆就表示過,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伍迪艾倫的灰色電影。他本人的精神狀態,和他的早期MV里所呈現的也是相差無幾。
十年前,陶喆因為出軌PPT事件遭遇了職業生涯的滑鐵盧,公眾形象一落千丈的同時,也留下了“一秒4破”的車禍現場記錄。在那之后,陶喆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不怎么發歌也不咋演出,在油管上做起了編曲教學。
直到近年來,他才逐漸回到大眾視眼。現如今,經歷過華語樂壇黃金年代的80后、90后們,大家再也不用為評論區那句“陶喆是誰?”而感到刺痛了,因為歸來的他已經登上了抽象文化的頂峰。看似被玩梗、被玩笑,但聽著他音樂長大的人都知道,無一例外,這些人最后都會成為他的樂迷。
“喆學”讓陶喆成功翻紅,這背后的邏輯不是因為他蹭到了抽象文化的熱度,而是因為教父級別的音樂作品和松弛自然到時而“脫線”的唱作者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這場屬于陶喆的文藝復興,注定了不可復制,甚至很難被超越。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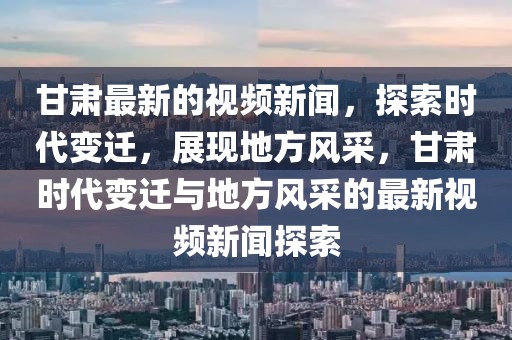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