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和北非事務協調員布雷特·麥格克、負責近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芭芭拉·利夫訪問沙特阿拉伯,為推動以色列與沙特達成協議展開進一步斡旋。同日,由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局長埃利·埃斯科濟多率領的以色列代表團抵達沙特阿拉伯參加聯合國世界遺產會議,其中也包括外交官員,這是以色列政府多年來對沙特的首次公開訪問。
對此,新華社援引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推動以沙關系正常化有其地緣戰略和國內政治考量。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也據此采訪了多位相關領域的權威學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劉中民告訴記者,推動沙以關系正常化是美國在試圖“兩頭抓盟友”,沙特和以色列都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與兩國的關系都在近年出現波動,此時推動沙以關系正常化是美國希望改變對其越來越不利的中東局勢的體現。
鑒于中東關系的歷史性調整空間,各方仍在猜測達成任何協議的框架。以色列外長埃利·科亨表示,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與沙特達成和平協議”,但沙以建交仍面臨重重障礙,短期內恐怕難以“一蹴而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牛新春向澎湃新聞指出,目前美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有比較強烈的愿望來實現沙以建交,但各方開出的條件差異仍然很大。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鄒志強則表示,當前美國政府在斡旋沙以建交上面臨比較大困難,主要障礙在于沙以兩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差異,沙特將實現巴勒斯坦建國作為承認以色列的前提條件,以色列如果不在尊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問題上做出有效讓步,沙特作為阿拉伯國家的“領頭羊”,很難邁出正式承認以色列的步伐。
沙以離正常化還有多遠?
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鮮有中東國家承認其地位。2002年,沙特帶頭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宣布阿拉伯世界承認以色列的條件是以色列從占領區撤軍,并承認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東耶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
因巴勒斯坦問題和阿以沖突的存在,包括沙特在內的多數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一度相互對立甚至敵視。新華社指出,在美方撮合下,自2020年以來,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4個阿拉伯國家相繼宣布同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次年,以色列極端民族主義執政聯盟的司法計劃引發了該國前所未有的不穩定局勢,美國斡旋沙以關系的進程停滯不前。
牛新春在6月29日發布的文章《沙特與以色列建交漸行漸近》中指出,2020年8月“亞伯拉罕協議”簽署以后,以色列和美國都把沙特作為下一個主攻目標,但是沙特一直態度含糊、行動搖擺。近期,沙特外交出現大幅度調整,沙以關系突破的可能性大增。同時,沙以建交不是只有沙特和以色列兩大主角,還有美國這個重要的玩家,沙特、以色列和美國構成了一個三角關系。美國目前的熱情也比較高。
當地時間9月7日,在美國總統拜登飛往印度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之際,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沙利文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表示,美國、以色列和沙特領導人已經提出了通往“正常化道路”的許多要素,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對許多關鍵要素有了廣泛的了解,但我們沒有一個框架,沒有準備好要簽署的條款。”沙利文說。
沙以兩國的“民間互動”同時出現逐漸回暖的積極跡象。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9月10日,以色列政府官員組成的一個代表團11日在沙特阿拉伯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大會。據報道,領頭的是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局長埃利·埃斯科濟多,另外還包括以色列外交官員,這是以色列政府多年來對沙特的首次公開訪問。
此次以色列代表團的訪問正值美國推動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關系正常化的斡旋期間。有報道認為,近年來,出于對伊朗的“共同懷疑”,沙以兩國已經悄悄培養了關系,“閉門討論外交和安全議題”。沙以雙方達成正式協議將是以色列融入更廣泛的中東地區的歷史性一步,但目前仍面臨著重大挑戰。
拜登政府希望借此彰顯外交成果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致力于達成一項里程碑式的協議,將在沙特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建立外交關系作為一項首要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美國2024年即將舉行大選,在中東地區“少有作為”的拜登政府希望借此彰顯外交成果,為大選做準備。
鄒志強表示,美國希望以色列和沙特這兩個中東地區的關鍵盟友實現建交,以提升本屆政府政績和服務于國內選舉,并集中力量應對大國競爭。為此美國拜登政府加大了斡旋力度,當前是沙以關系正常化的積極推動者。
此前在中方支持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于3月6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對話。10日,沙伊兩國達成北京協議,中沙伊三方簽署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系,開展各領域合作。
牛新春表示,在全球政治層面上,沙特與伊朗復交令美國感到不安,因此美國認為若能夠斡旋沙特與以色列建交,則能扳回一局;在地區層面上,美國對沙特與伊朗復交、敘利亞重返阿拉伯社會、伊朗核能力增強等事情感到憤怒,其認為若沙以能夠建交,則有助于減輕美國壓力;在國內政治層面上,美國認為若能斡旋沙以建交,這將成為拜登政府最亮麗的外交成果,是送給2024年大選的大禮包。
白宮上周證實,由拜登特使布雷特·麥格克率領的美國代表團本周將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進行會談,以“解決一系列廣泛的地區問題”,包括也門正在進行的戰爭,預計也會討論可能達成的關系正常化協議。負責近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芭芭拉·利夫、美國也門問題特使蒂姆·倫德金一同出席。此前,以色列高級外交代表團曾訪問美國,磋商以色列與沙特關系正常化協議的大綱。
劉中民指出,美國推動以沙關系正常化有其地緣戰略和國內政治考量。“當前中東地區格局變了,特別是在中東國際關系緩和潮,即沙特伊朗關系緩和之后,美國有日趨被邊緣化的態勢。”劉中民認為,美國這些年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呈收縮趨勢,“推不動伊核協議,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既無心也無力。美國在中東的抓手非常有限”。
前任總統特朗普曾推動以色列與摩洛哥、蘇丹、巴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達成了“亞布拉罕協議”,如此時再與中東大國沙特取得關系突破,將進一步改變中東地區政治格局。然而,拜登曾于今年7月初表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距離正常化協議“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據信該協議將包括一項美國-沙特防御條約以及美國為沙特提供民用核項目。
巴勒斯坦問題成關鍵
美國前幾任政府,例如卡特政府和克林頓政府都想以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為抓手,來同時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比如1979年卡特政府推動的以色列和埃及關系正常化,克林頓政府在1990年代中東和平進程中推動的以色列和約旦關系正常化。到了2000年以后,巴以沖突加劇,美國在“9·11事件”后轉向反恐行動,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越來越“無能為力”。
劉中民表示,目前的巴勒斯坦面臨著三個層次的困境:第一個層次,巴勒斯坦問題在國際社會上被嚴重的邊緣化,除了中國仍在聯合國不斷提及巴勒斯坦問題外,其他國家對該問題已經不再重視;第二個層次,阿拉伯國家也開始分開看待巴勒斯坦問題,即在輿論上支持巴勒斯坦,但仍跟以色列發展關系;第三個層面是巴勒斯坦內部困境,如今巴以沖突已經成為常態化的存在,小沖突不斷,巴勒斯坦和哈馬斯的分歧也始終存在。因此,不論是國際社會的多邊機制層面,還是巴以自身的關系狀態,以及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都導致巴勒斯坦處于困境之中。
本周早些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分別與巴以領導人通電話,討論了與沙以關系正常化協議相關問題。在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通話時,布林肯“重申美國支持采取措施,促進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和安全,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說,布林肯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討論了類似問題,同時重申了“雙邊伙伴關系的力量和美國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米勒同時表示,即使有這樣的兩通電話,美國也“不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會有任何即將宣布的消息或突破”,表明沙以關系正常化目前仍是一個難以落地的愿景。
鄒志強指出,近年來,為在新形勢下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沙特也希望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但這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妥協,既要以色列承認和保障巴勒斯坦國家地位與主權的權利,也希望巴勒斯坦方面能夠接受與以色列的和解。目前來看,以色列不愿做出實質性讓步,巴勒斯坦方面也對此態度悲觀,不愿意成為被犧牲對象,雙方關系很難緩和。
“美國希望沙以兩國能夠通過和談實現建交目標,但缺少有效手段調和沙以雙方的立場分歧。這需要美國政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推出明確有效的方案和足夠投入,對雙方可能達成的和解方案進行擔保。以色列可能會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做出某種承諾,為沙特提供建交的正當性理由;沙特將不會堅持其原有全部訴求,在安全、投資、技術等方面獲得以色列的支持。”鄒志強說。
據媒體報道,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拜登政府加緊努力,試圖確保美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達成三方協議,擬議的協議將涉及沙特阿拉伯承認以色列,以換取美國政府的大規模安全保證以及最終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一些保證。在美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三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數億美元的現金刺激和對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土地的控制權是巴勒斯坦的要求之一。利雅得方面堅稱,任何協議都必須包括推動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努力,以色列迄今斷然拒絕了這一讓步。有媒體分析稱,協議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讓人看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做出了重大讓步。
對此,牛新春表示,一方面,美國需要給予沙特豐厚的獎賞,另一方面,以色列也需要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做出象征性讓步。據媒體披露,沙特開出了一些條件,包括同美國簽署正式的同盟條約,從美國購買更先進的武器,要求美國同意沙特發展民用核能力等。與此同時,沙特也向以色列開出了價碼,要求以色列凍結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建設,給予阿克薩清真寺更大的自治權。近期,美以媒體充斥的有關美沙、沙以交易的各種細節報道,似乎都在預示著沙以建交正“漸行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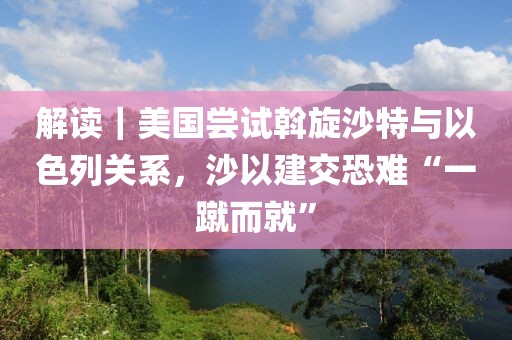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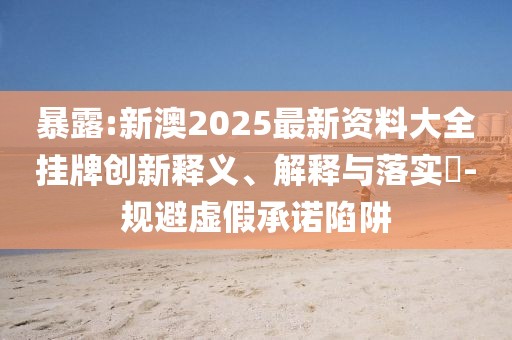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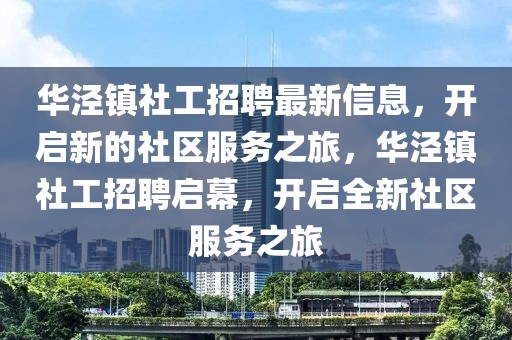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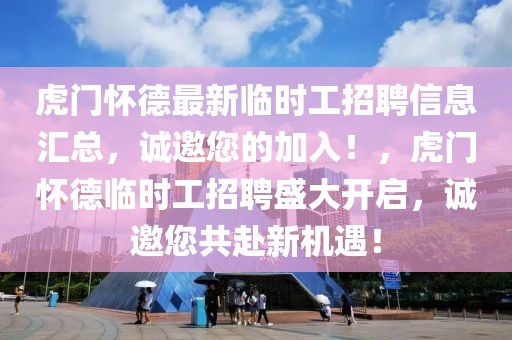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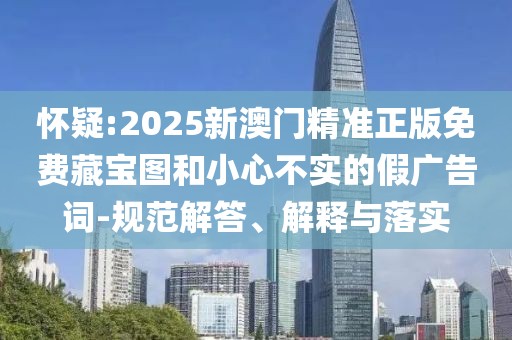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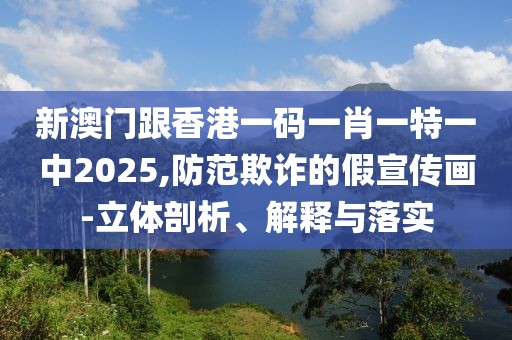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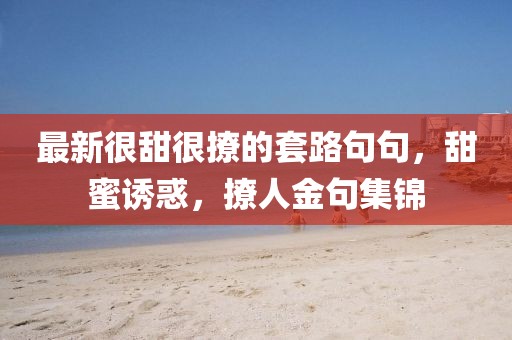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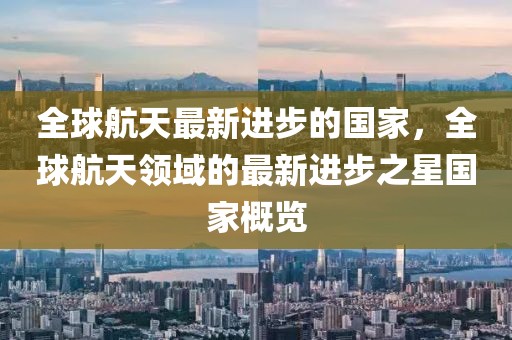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