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保生 朱媛媛 肖強 金杜律師事務所爭議解決部
近年來,隨著證券監管機構對資本市場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及其他市場主體因信息披露違法而被投資者提起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訴訟。
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只有在虛假陳述實施日之后買入股票,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未賣出股票的投資者,才可能獲得賠償。在多數虛假陳述訴訟案件中,各方對于實施日的認定一般爭議不大,揭露日的認定通常具有決定意義。由于各地法院認定標準的不統一以及不同案件的特殊性,揭露日的確定往往成為此類案件的主要爭議焦點。
本文將在介紹證券虛假陳述揭露日的基本內涵和法律意義的基礎上,結合法院判例對司法實踐中揭露日的認定標準和常見情形進行分析,并著重就各類揭露日的認定要點進行歸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法釋[2003]2號,下稱“《若干規定》”)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虛假陳述揭露日,是指虛假陳述在全國范圍發行或者播放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上,首次被公開揭露之日。”
所謂揭露,通常是指監管機構、交易所、新聞媒體或者其他外部力量對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虛假陳述行為,通過立案調查、擬處罰、行政處罰、新聞報道、采取監管措施等方式向投資者予以公開化,而揭露日則是指虛假陳述行為在全國范圍發行或者播放的權威媒體上被首次公開的日期。
揭露日作為將證券虛假陳述行為所掩蓋的真相公開揭示之日,不僅對證券市場和證券投資者具有風險警示作用,而且在判斷投資損失與虛假陳述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若干規定》第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人民法院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即為投資人系在虛假陳述實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買入該證券。根據《若干規定》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如果投資者在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經賣出證券,或者在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進行投資,則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若干規定》實際上是基于“欺詐市場理論”推定,在虛假陳述對市場產生影響的時段內進行相關證券交易的投資人,是基于對虛假陳述的信賴而進行的交易,因此產生的損失與該虛假陳述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而《若干規定》第十八條與第十九條之所以以揭露日為界限,將揭露日前賣出證券、揭露日后買入證券的交易行為排除在認定存在因果關系的范圍之外,是因為揭露日前虛假陳述行為尚未被公開,此時投資者賣出證券所導致的損失,往往是由于證券虛假陳述之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而揭露日之后虛假陳述的欺詐性已經不再作用于交易行為,此時買入證券所導致的損失,實屬投資者決策失誤、甘冒風險的后果。
根據《若干規定》第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認定虛假陳述揭露日時,一般應考慮揭露內容的相關性、揭露主體的權威性和揭露時間的首次性,此外,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通常還會考察揭露行為是否對證券價格造成了影響。
如前所述,揭露的意義在于向證券市場和證券投資者釋放警示信號,因此,在確定揭露日時,首先應當考察揭露行為是否與虛假陳述行為相一致,能否充分揭示投資風險。
例如,在大智慧案[1]中,對原告關于以立案調查公告日為揭露日的主張,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該公告的內容僅提及“公司信息披露違法涉嫌違反證券法律規定”,并未指出信息披露涉嫌違法的具體表現和具體內容,故對于投資者而言,僅閱看該公告并不必然會將其與公司2013年年報建立聯系,客觀上不具備受到足夠警示的條件,因此,該公告日不應作為揭露日。
《若干規定》將虛假陳述公開途徑限定在“全國范圍發行或者播放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上”,這是因為全國性的媒體具有受眾廣、傳播快、可信度高等特點,能夠最大限度地起到警示作用。如果虛假陳述是以公司公告形式揭露的,由于上市公司必須在證券監管機構指定的信息披露網站或報刊(如《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上海證券報》、上海交易所網站、深圳交易所網站、巨潮資訊網)上披露公告,因此,以公告日作為揭露日的情形通常不存在“揭露主體權威性”的爭議。
但是,在以新聞媒體報道日作為揭露日的情況下,就需要著重考慮揭露媒體的權威性。例如,在康芝藥業案[2]中,對于原告關于21世紀網數字報發布某篇報道的日期為揭露日的主張,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該媒體不符合“全國范圍發行媒體”的要求。
當然,對上述限定不能做絕對化地理解。在資訊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一些地方傳媒發布的消息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通訊手段,迅速傳達至全國各地的受眾。因此,如果一家非全國性媒體對某虛假陳述行為進行了揭露,而該報道又被各大門戶網站廣泛轉載,進而導致了相關證券價格的異常波動,表明這一報道也具備了全國性的影響,則該地方媒體的報道亦可作為確定揭露日的依據。
對虛假陳述行為的揭露往往有一個過程,期間可能會先后出現多次程度不同、來源各異的公告消息或者新聞報道。一般來說,利空信息首次公開后對證券價格的刺激最為強烈,而在之后風險釋放的過程中,即使這種利空信息不斷被重復或強化,市場反應一般也有限。
因此,《若干規定》強調了揭露日的“首次性”,以最大程度地把因虛假陳述行為被揭露導致股價下跌而產生的損失計入可索賠范圍,從而起到保護證券投資者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通常也會將“揭露行為”是否對相關證券價格產生影響作為判斷揭露日的標準之一,如果“揭露行為”發生后證券價格并無異常波動,就難以說明證券市場對該揭露行為有所反映,也就難以證明該揭露行為起到了足夠的風險警示作用。
我們理解,《若干規定》之所以未將“導致證券價格異常波動”作為確定揭露日的條件,可能是因為在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中,揭露日后證券價格發生異常波動是不言自明的環節,沒有異常波動投資者就不會產生損失,投資者不會產生損失就不會形成索賠之訴。
根據判例研究,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通常將如下日期認定為揭露日:上市公司被立案調查公告日、處罰事先告知書公告日、收到處罰決定公告日、媒體揭露報道發布日、上市公司自我揭示日、收到監管措施決定公告日等等。
實踐中,被立案調查公告中一般會披露上市公司被立案調查的原因,并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但是,公告披露的被調查的原因往往被籠統概括為公司涉嫌虛假陳述、公司存在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甚至只提及公司涉嫌違反證券法律法規,并不會就虛假陳述的具體情況作出說明。
因此,被立案調查公告所揭露的內容與最終處罰的虛假陳述行為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往往成為案件的爭議問題。審理法院一般會以公告內容與最終的處罰決定內容一致、前后呼應為由,認定被立案調查公告滿足揭露內容的相關性要求。
例如,在大唐電信案[3]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證券監管機構最終對大唐電信及其相關責任人作出行政處罰的結論性事實,與立案調查公告的內容前后呼應,完全相符,證券監管機構只有在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的前提下,才能對涉嫌違法違規主體進行立案,并且,立案調查公告已經明確寫明“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因此,立案調查公告具有較強的警示作用,足以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應當認定為揭露日。
又如,在南通科技案[4]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南通科技公告的上海稽查局將對公司涉嫌違反證券法規行為進行現場調查的事項,與涉案虛假陳述有直接的關聯。
再如,在協鑫集成案[5]中,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立案調查公告雖然文本簡潔,但措辭嚴厲,且公告表明證券監管機構是在公司自查整改后仍然決定對公司未按規定披露信息進行立案調查,已具備足夠的警示強度以提醒投資者重新判斷股票價值。
根據規定,證券監管機構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之前,會向上市公司下發《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告知書會就證券監管機構認定的違法事實、理由和依據作出詳細的說明。因此,上市公司收到處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往往會起到充分揭露虛假陳述行為的作用,而公告發布之日也就經常會被認定為證券虛假陳述揭露日。
例如,在九發股份案[6]、大智慧案中,人民法院判決均將上市公司收到《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當日認定為揭露日。
通常而言,一旦被證券監管機構立案調查,上市公司不僅要發布臨時公告披露調查事宜,還應根據調查進展和自查情況發布更正公告,而且各大新聞媒體也會爭相報道,追蹤事實真相,因此,在《行政處罰決定書》正式作出之前,證券虛假陳述行為很有可能已經被揭露或者更正。
在早期的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多數人民法院判決(例如,紅光實業案[7]、九州股份案[8]、長江水運案[9]、豐華股份案[10])將上市公司收到行政處罰決定公告之日認定為揭露日,其主要理由,或者是因為上市公司沒有就相關證券虛假陳述發布更正公告,或者是因為此前的更正公告、新聞報道不足以構成對虛假陳述行為的實質性揭露。
例如,在九州股份案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九州股份沒有對行政處罰決定中涉及的虛假陳述行為進行自我更正,而直到行政處罰決定公布后,九州股份虛假陳述的事實才首次得以公開披露。
又如,在豐華股份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上海證券報》報道的“*ST豐華董事集體下課”的內容,主要是聚焦被告200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進程以及股東之間的爭執。該報道不構成對豐華股份虛假陳述行為的首次實質性揭露,同時該報道的內容與處行政處罰決定事項亦不存在同一性和關聯性。
新聞媒體對于上市公司存在財務造假等虛假陳述行為的披露報道,往往會引起廣大股民和證券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進而成為上市公司被立案調查并最終被行政處罰的導火索。而上市公司被立案調查后,新聞媒體的事件揭秘、跟蹤報道又往往能發掘出鮮為人知的驚天內幕,將虛假陳述行為公之于眾。
然而,并非所有對上市公司不利的新聞報道均可以被認定為對虛假陳述行為的揭露。相比于上市公司自行發布被立案調查公告、收到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公告及收到行政處罰決定公告,新聞媒體的揭露報道存在著揭露媒體是否權威、報道內容是否屬實、揭露事項與最終的行政處罰事項是否一致等諸多問題。因此,人民法院在將新聞媒體的揭露報道發布日認定為揭露日時,往往要著重考慮揭露媒體是否為全國性的權威媒體以及揭露內容是否與行政處罰事項具有一致性。
例如,在紫鑫藥業案[11]中,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在多個不同的報道中確定其中一個報道為揭露日的原因是,該報道內容詳盡而且有記者的實地踏查和親自調研,經新華網轉載后被大量傳播。而其他報道則由于不具有相關性、可信度,或者未對證券價格產生影響等原因,被審理法院認定為不符合揭露日的立法本意。
又如,在宋都股份案[12]中,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將《京華時報》發布題為《國能集團四高管被罰市場禁入》報道之日認定為揭露日,主要是因為該報道發表在先,且能對國能集團2005至2008年年度報告存在隱瞞重大關聯交易及虛假記載等多項違法違規事項進行揭露。
根據《若干規定》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上市公司自行公告更正虛假陳述并按規定履行停牌手續之日應認定為更正日。事實上,“揭露日”和“更正日”的本質都是對虛假陳述行為的“揭示”,將事實真相公之于眾。在某些案例中,人民法院將上市公司自行發布公告揭示虛假陳述行為的日期確定為“揭露日”而非“更正日”。
例如,在寧波富邦案[13]中,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將寧波富邦發布《涉及訴訟公告》披露涉及訴訟情況之日認定為揭露日。又如,在銀河高科案中,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將銀河高科公告發布《董事會澄清公告》,披露其虛增收入和利潤、大股東占用資金及銀行貸款余額賬實不符等問題之日,認定為揭露日。
雖然證券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采取的行政監管措施不屬于行政處罰,但是出具警示函等監管措施往往可以起到揭露虛假陳述行為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證券市場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征求意見稿中,也將信息披露義務人因虛假陳述被交易所或證券監管機構采取監管措施作為認定揭露日的情形之一。
例如,在佛山照明案[14]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佛山照明發布《關于收到廣東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的公告》,系首次向投資者公布其因虛假陳述被行政處罰,故該日為虛假陳述揭露日。又如,在友利控股案[15]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友利控股發布《關于收到四川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的公告》之日為虛假陳述揭露日。
對司法實踐中虛假陳述揭露日的司法判例進行系統化的梳理和分析,是構建科學、合理、統一的揭露日認定標準的基礎與前提。《若干規定》關于虛假陳述揭露日的規定更側重于揭露行為的表現形式,而對于更為重要的認定原則、認定標準等實質內容則規定的較為模糊、籠統。有鑒于此,我們將在本文的基礎上,推出新的文章,結合司法實踐就完善虛假陳述揭露日的認定標準提出我們的建議。
針對證券合規和證券訴訟案件多發的現狀和當事人對該類糾紛專業化法律服務的需求,金杜律師事務所組織了由多位合伙人和資深律師組成的證券合規和證券訴訟服務團隊,專門為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基金公司及其董監高提供專業的證券合規和證券訴訟法律服務。近年來,金杜律師事務所的證券合規和證券訴訟服務團隊先后協助數十家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處理了大量的證券合規和證券訴訟業務,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客戶的信任和高度認可。
[1] 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01民初679號《民事判決書》。
[2] 參見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第77號《民事判決書》。
[3] 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初字第5783號《民事判決書》。
[4] 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蘇民二終字第0112號《民事判決書》。
[5] 參見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蘇01民初151號《民事判決書》。
[6] 參見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煙商初字第79號《民事判決書》。
[7] 參見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成民初字第871號《民事判決書》。
[8] 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閩民終字第348號《民事判決書》。
[9] 參見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06)渝五民初字第37號《民事判決書》。
[10] 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7)滬一中民三(商)初字第68號《民事判決書》。
[11] 參見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長民四初字第74號《民事判決書》。
[12] 參見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初字第159號《民事判決書》。
[13] 參見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甬商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書》。
[14] 參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
[15] 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終732號《民事判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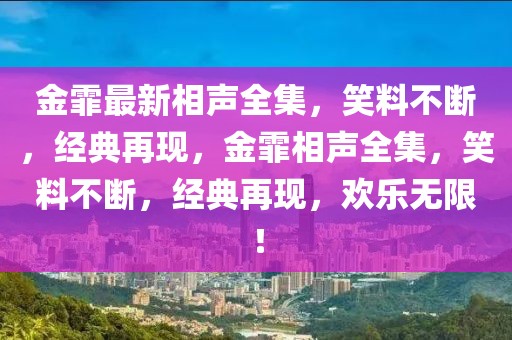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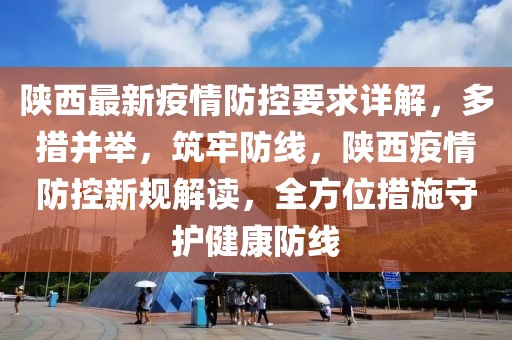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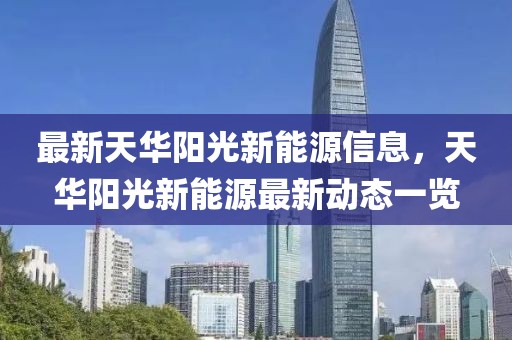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