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墻的燈光正在亮起,一位掌燈者的人生已經黯淡。
10月15日,據中央紀委網站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委書記豐立祥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兩天后,其山西省人大代表職務被罷免。
消息很快傳遍大同每一個角落,放炮成為一些大同人表達喜悅的最直接方式。與此同時,另一位官員的名字再次被頻繁提起。
他是耿彥波,曾和豐立祥搭班,擔任大同市長,2013年2月赴太原擔任市委副書記、市長。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在大同采訪時了解到,迥異于豐立祥,耿彥波在大同享受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一些大同人極盡溢美之詞,表達對“耿市長”重返大同的渴望。
一位是落馬書記、一位是明星市長,很少有一個城市像大同這樣愛憎分明。近乎整齊劃一的聲音背后,是民望與官聲的考驗,亦是城市命運的選擇。
盼與怨:書記與市長的“冰火兩重天”
10月18日,大同東城墻腳下,近千名群眾聚集在和陽門廣場。廣場四周是嚴陣以待的警察,中間是“大同市公安機關維穩處突拉動演練”的條幅。
10月18日上午,千余大同市民聚集在大同和陽門廣場,希望原市長耿彥波重返大同。
走進人群當中,很快就會明白這些人的來意。
“他在大同這幾年,啥也沒干,還是把耿市長調回來當書記吧。”聚集的人群肆無忌憚地數落豐立祥的不是,同時表達對耿彥波的贊許。
這是豐立祥“落馬”后的第一個周六,整座城市仍處于一種“亢奮”的情緒之中。
“你沒見15號,跟過年一樣,PM2.5估計都激動地爆表了。”古城墻附近的煙花爆竹銷售點前,一個小伙子喜滋滋地曬出業績——當天下午,他的收入比以往多了三成。
根據多位受訪者事后的描述,豐立祥被調查當天下午,大同市區的街頭、小區、市委大院門口乃至市政府家屬院里都響起了連串炮聲。
一天后,一則主要內容為10月18日上午9點在和陽門廣場為“耿市長”請愿的消息通過網絡、微信以及口口相傳被廣泛傳播。
當天上午,近千人陸陸續續趕來,到中午時分才陸續散去。
這便是被譽為“三代京華、兩朝重鎮”的大同,曾經是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族融合的中心。
自己落馬引發民眾歡慶,這是豐立祥一定不會想到的結局。這位出生于1957年的山西朔州籍官員,2006年4月調任大同,8年期間先后擔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以及市委書記。
這也是大同改頭換面的8年。2008年,大同全面啟動古城保護,陸續修復古城墻、四合院等歷史文物。2009年,以魏都大道為首的全市21條道路開始修建或新建。2013年,代表大同新貌的御東新區五大場館主體工程全面完工,曾經的“大縣城”終于露出都市面貌。
大同人更多地將這些成績歸功于豐立祥的前任搭檔、大同原市長耿彥波。
這位曾在山西靈石、晉中、太原等地任職的山西晉中籍官員,2008年調任大同。
在擔任大同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期間,他推動了城市拆遷、道路新建、古城修復等多方面的工作,也曾因為超乎常規的“大同速度”在全國引發爭議。
和耿彥波面臨的爭議相比,豐立祥得到的評價近乎“一邊倒”。
不少大同人指責他當市長時庸庸碌碌,沒做成什么事兒。
一個例子是,2006年,豐牽頭修過一條連接市區和同煤集團的大慶路。作為當時的“樣板工程”,這條路修了兩年,通車沒多久又變得坑坑洼洼,工程質量頗讓人失望。
澎湃新聞檢索新聞報道發現,豐立祥主政大同期間也曾做過不少表態和努力。
比如,他提出過“轉型發展、綠色崛起”的理念,力圖改變當地“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他熱衷于深入周邊區縣調研,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
豐立祥對大同古城的修復建設也給予支持,多次強調古城墻合攏要加快進度。即將在今年11月開工建設的大(大同)張(張家口)高鐵,也得益于豐立祥的推動。
不少大同人對他還是不買賬。多位接近過他的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豐立祥做事中規中矩、能力一般,是位缺乏個性的官員。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一位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豐立祥表面和和氣氣,只求安穩做官,很少得罪人。平時別說開會,就是和工作人員一起吃個飯,他也只會講一些浮于表面的客套話,十足的官員做派。
另一位知情人士則透露,豐立祥家住太原,每周五下午都會趕回200多公里外的省城,通常周一下午才會出現在市委大院。這個習慣除非有上級領導來,一般不會打破。
因此,雖然在大同主政多年,他在當地仍顯得面目模糊,似有似無。很多人對他的落馬都感到詫異,理由是印象當中,他做過的事情太有限。
特別是在大同任職兩年后,豐立祥迎來了新的工作搭檔耿彥波。
耿彥波是山西晉中和順人,比豐立祥小1歲,以個性鮮明、性格火爆著稱。調任大同后,他以強勢作風掀起了“造城運動”。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覺得好多官員都不行。”多位與大同市政府接近的人士坦言,耿彥波是個“工作狂”, 每天從早到晚什么都抓,而且事無巨細、身體力行,這也使他的風頭很快全面蓋過豐立祥。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耿彥波在2009年寫過一篇《大同賦》。這篇作品初次亮相就在大同城鄉規劃展覽館,之后成為當地文化標志之一。2012年,大同大學書法專業師生曾用各種書體書寫《大同賦》并舉辦主題展覽,作為大同市長的耿彥波出席了開展儀式。
多位大同官員對澎湃新聞表示,表面看來,兩人相處還可以,不像外界傳的那么糟。特別是大同這幾年在城建方面取得的成績,沒有豐立祥的配合和忍讓,耿彥波也無法順利開展工作。
“平時遇到關鍵性問題,他們也會互相商量,比如2009年云岡石窟景區因違法建設被國家文物局緊急叫停,這個困難也是兩人共同面對并解決的。”多位大同官員回憶。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的關系似乎又有些微妙。
一位接近大同市委的知情人士告訴澎湃新聞,耿彥波事情多,總在現場辦公,經常不參加市委常委會議。這一行為也被旁人解讀為不把書記放在眼里。
豐立祥也在試圖“捍衛”自己的“一把手”地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豐立祥十分注重自己的媒體曝光率。有關他的報道如果出現錯別字,豐立祥本人馬上就會發現。
他還曾因為耿彥波經常上“頭條”而自己的新聞比較少感到惱火。為此,當地媒體特別做了調整——盡可能增加書記的內容。如果書記和市長同一天各自有活動,必須確保書記的版面。
“后來只要有豐立祥的新聞,耿彥波就基本上不了頭條。”這位知情人士告訴澎湃新聞。
走與留:一紙調令激發的民望與官聲
“上頭條”的尷尬在2013年2月結束。
2013年2月7日,山西省委任命耿彥波為太原市委副書記。緊跟著第二天,太原市人大常委會任命耿彥波為太原市副市長,代理太原市長。
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讓不少大同人感到意外。大同市規劃部門一位工作人員對澎湃新聞回憶,2013年2月3日,他們還在向耿彥波匯報新一年的工作計劃,沒有發現任何市長要調走的征兆。
也是在2月3日這一天,《大同日報》頭版刊登了耿彥波被山西省委組織部確定為“市委書記”考察對象的公示。
這是繼2011年12月后,耿彥波第二次被列為“市委書記”考察對象,這個信號也被各界普遍認為,他將接替豐立祥出任大同市委書記。
因此,當耿彥波調任太原的消息傳出,一場聲勢浩大的挽留請愿活動在大同爆發。
請愿從2013年2月12日開始,持續近一周,其中不乏市民下跪、打橫幅、喊口號等舉動。
“剛開始市委、市政府也不知道怎么辦,只能先給省里匯報。”一位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回憶,請愿活動進行到第五天左右時,時任山西省委副書記金道銘深夜趕到大同傳達省委指示,將這一活動定性為“非法集會”。
時隔一年半多,當金道銘、豐立祥先后落馬,山西省委原書記袁純清調離后,另一位接近當地政府的人士仍表達了謹慎的看法。
他告訴澎湃新聞,當時參加請愿的人大多數都是出于自愿。只不過,請愿開始的時間是大年初三,在大同這樣的三、四線城市,其時照片沖洗店、打印店基本都關門了。一夜之間能出現大量條幅、標語和照片,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
這個疑惑“絲毫”不會撼動耿彥波在一些大同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離開大同1年零8個月后,10月22日下午,數十位老者聚在大同古城四牌樓附近,熱議對象依然是“身邊的政治”。
“老耿來的5年,大同變化比過去30年都多。”年過50的老劉至今還住在古城內的棚戶區。他說,如果不是耿彥波去年調走,拆遷慢下來,今年冬天也能住進有暖氣的樓房了。
73歲的老段對耿彥波“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充滿欽佩。大同有句話叫“見市長比見局長容易”,包括他在內,很多人都見過在工地忙碌上的耿彥波。
在數十位老者的記憶中,耿彥波面容清瘦、皺著眉頭,穿一雙落滿灰塵的舊皮鞋,老百姓當面找他反映問題總能當場解決——這與傳統語境下的“清官”形象幾近吻合。
耿彥波留給不少大同市民的好感,也讓豐立祥處境頗為被動。
在大同的8年時間里,豐長年在市委的辦公室,老百姓很難見到本人。新聞報道中的他基本都是在開會發言,對普通市民來說基本上沒有吸引力。
這也是中國地方執政者一個很常見的景象。書記和市長,本是市委和市政府的“一把手”。前者是黨內職務,定基調、統攬大局、掌管人事;后者是行政長官,負責具體行政事務。
他們分工不同,贏得的關注度也有所不同。這也是為官之道的一門“學問”,有人重視上級評價,懂得經營“官聲”,有人熱衷深入基層,善于積累“民望”。
當耿彥波被調離的消息傳出,“民望”再一次集中爆發——不少參與2013年初請愿活動的大同人認為,是豐立祥占著書記的位置,耿彥波才不得不離開。當時亦有人編出“空談誤國豐立祥、實干興邦耿彥波”的段子,揶揄這位當時的市委書記。
“人事任命最終還是省里決定的,老百姓的心情能理解,不過看法還是太偏頗了。”當地一位政府官員頗有些無奈。
礙于身份,他不愿對豐、耿二人做更多評價,但也承認,耿彥波在他心目中堪稱“完美”。
挺與倒:為城市發展犧牲的大同人
在“挺耿派”眾多的大同,王建是個異類。
他原本住在古城內北城墻腳下,2011年9月遭遇強拆,期間還因為言論不當、行為過激被公安機關拘留多次。
王建反對拆遷的理由很簡單,補償不合理。政府給的補償標準時拆一平米補一平米,安置房的面積如果超出標準,要按相應的階梯價格購買。
“大紅本的房子,2002年左右買的,政府要拆,裝修沒有補償,搬到城外也不算地段差價。”因為不接受安置條件,王建帶領他所在小區的近百拆遷戶硬扛了大半年。他也曾攔住耿彥波當面表達訴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堅持到最后的王建在拆遷前一天分到了相對理想的安置房,之后政府還以困難補助的形式拿出11萬元作為補償。
可王建并不打算罷休。他覺得如果不是自己態度強硬,就會和大多拆遷戶一樣,租房、排號、等待新房分配、貼錢買房,住到距離老城七八公里的地方。
“到現在為止,還有不少2012年、2013年拆遷的人沒住進安置房。”王建決定用鏡頭記錄古城拆遷。一年多期間,他至少見證了50起強拆,其中包括自焚、跳樓等抗拆事件。
這些親眼目睹也讓王建越來越失望。在他看來,古城雖然氣派了,但是缺少了原始的人煙味兒,城市雖然靚麗了,但建起來的多是高樓大廈,和真正的老百姓生活離得太遠。
像王建這樣堅定的“倒耿派”,在大同略顯孤單。過去幾年,相當數量大同市民遭遇拆遷,但大家的態度多為無奈,或抱著顧全大局的想法。
“畢竟環境好了,城市有變化了。”一位曾住在古城華嚴寺旁邊的“拆遷戶”坦言,十多年前,大同人街上走一圈,鼻孔都是黑的,如今馬路寬敞、干凈了,空氣質量也排到了全省第一。就沖這個,個人吃點虧不算什么。
“大同人深愛大同的歷史文化,懷有濃烈的古都情節。”大同市古城保護和修復研究會會長安大鈞告訴澎湃新聞,1972年,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大同的周恩來總理曾表揚大同的文物古跡沒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壞,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大同人很早就認識到古城的歷史文化價值。
大同市城鄉規劃專家委員會主任張滃也直言,為了古城,大同人確實做了不少犧牲。
據他介紹,大同曾是北魏首都,遼、金陪都。1982年,大同與北京、承德、南京等另外23座城市共同入選首批歷史文化名城。1984年,國務院批準大同市為全國13個較大的市之一,一同入圍的,還有大連、重慶、青島、無錫等。
這是大同的輝煌,也是大同的痛楚。最近30余年,由于國家戰略布局、煤炭產業的局限、主要領導更換頻繁等原因,這座城市的地位已經被邊緣化。
以最近兩年為例,大同GDP總量僅高于陽泉、忻州,位列山西省第九。今年7月開通的大(大同)西(西安)高鐵,實際只有太原至西安段通車。地處山西北部的大同,至今連動車都沒有通。
“看著資源枯竭、城市落后,大家也希望找一條新的出路。”張滃認為,不少大同人表現出對耿彥波的支持,說到底還是對家鄉發展的渴望。
快與慢:后“豐耿”時代的考驗
這種借古城改變現狀的想法至今未看到明顯成效。
根據大同市旅游局統計,今年“十一”黃金周,大同接待海內外游客294.7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約13億元,旅游接待量排在晉中、太原和運城之后,位居山西省第四。
“現在主要受制于交通,等高鐵通車,游客量肯定會增加。”在張滃看來,大同古城古樸、新城充滿張力,星級酒店等配套設施已經完善,旅游經濟將是大同資源匱乏一個重要補充。
這些美好愿景仍需要時間檢驗。在大同古城關帝廟附近,一位開飯店的女士正打算轉租商鋪。“平時沒什么人,就算來了,也就簡單轉轉,留不住。”據她介紹,這家店100多平米,年租金6萬,總體還是賺不到錢。
這座面積3.28公里的古城,曾是大同最繁華的地方,隨著拆遷和重建,商業全面萎縮,貼有“轉租”或“招商”的商鋪比比皆是。
一位老人站在貫穿古城東西的大西街頭感慨,“以前這兒是商業街,可熱鬧呢,現在野草都1米多高了。”
穿插在仿古建筑之間的,是破落的小巷和簡陋的平房。它們在“煥然一新”的古城景區顯得格格不入。
“水都停了,用水還要走十來分鐘去別人家挑。”王女士的家就在南城墻下的郵電巷。如果說當初讓搬走還有點猶豫不舍,留下來的住戶前所未有地盼著拆遷。
從她的家門口環顧四周,南面是恢弘的城樓,北面是新鋪的青石板路,面前兩米不到卻是一片廢墟。那本是去年8月拆掉的民居,拆完之后不了了之。
住在古城的居民也越來越感覺到生活不便。特別是政府為了環保,從去年起禁止在古城內燃燒原煤,要求使用型煤。住戶們普遍認為,型煤沒有原煤好用,做飯、取暖熱量上不來,到冬天就特別難熬。
同樣在等待的,還有部分和政府做生意的建筑施工方。一位參與古城燈光照明工程的人士透露,市政府迄今還欠著他們七八百萬的款項,類似情況在其他工程隊也普遍存在。
就在不少大同人都希望這股轉型發展的“陣痛”盡快過去時,聞名全國的“大同速度”卻隨著耿彥波離開放慢腳步。
西城墻修復兩年有余,至今仍未合攏。北城墻外的護城河,挖了填,填了又開挖。棚戶區的居民很久沒有聽到要拆遷的消息。修復完成的四合院大門緊鎖,巨大的廣告牌試圖將廢墟現場圍擋。
“他走了,很多事情都慢下來,甚至進行不下去了。”一位關注城市建設的大同市民表示,耿彥波通過個人能力給大同帶來了巨大改變,唯獨遺憾的是沒有建立起一個健康有序的機制。
大同人的擔心,政府早有察覺。早在去年2月,耿彥波的繼任者、大同市長李俊明上任之初就表達了“五個凡是”,承諾政府工作的連續性。
大同市規劃局一位現任領導也明確表示,兩任領導工作方式、風格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所有工作都在按部就班進行。目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正在編制古城保護規劃,預計明年出爐。
這座還在拼命追趕時代的古老城市,仍有許多“未完成”需要面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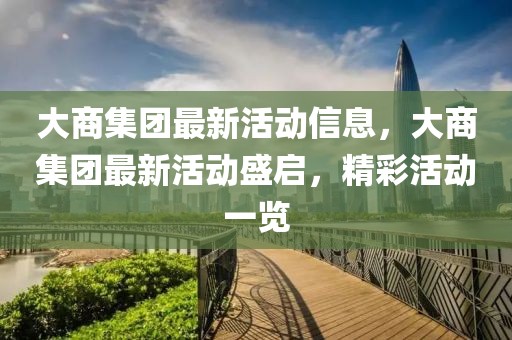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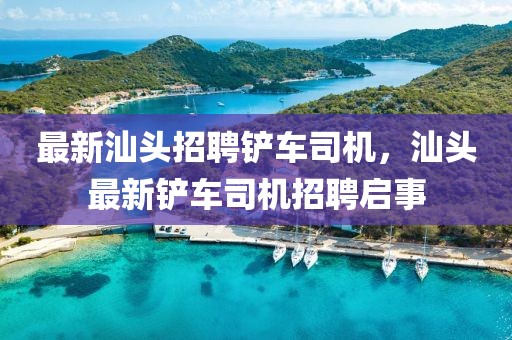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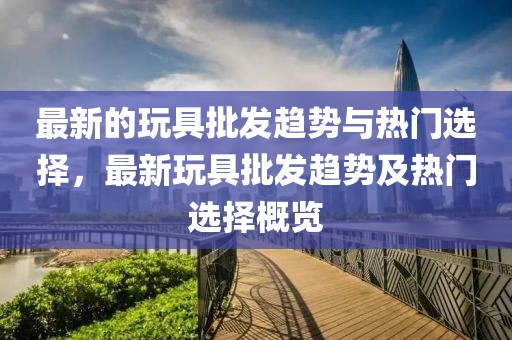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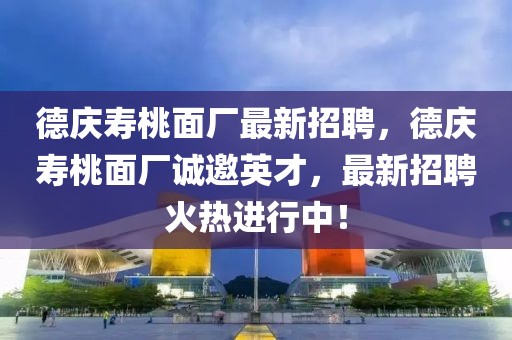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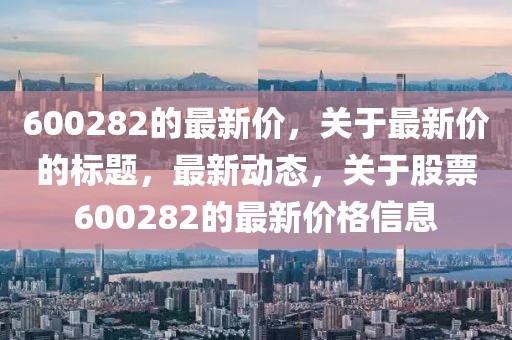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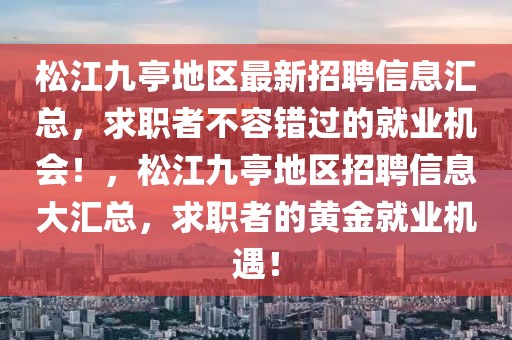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