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民生問題都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點話題。針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入園難、入園貴”現象,在近幾年的兩會上,出現了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呼聲。
隨著2016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在全面二孩時代,學前教育問題更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話題。基于“孕生養育教”壓力山大的現實,要想有效破解 “不敢生”現象,當然需要做好一系列配套保障措施,切實解決公眾的后顧之憂,而相對薄弱的學前教育無疑是首當其沖的重要環節。“上學難,上幼兒園更難;上一所好幼兒園,比上一個好大學、考研還難、還貴。”面對“孩奴”們的現實焦慮,又該如何化解呢?
基于此,在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李光宇、朱虹和全國政協委員姚愛興、朱玉華都相繼發出了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的強烈呼吁。這些體現民本情懷的聲音,堪稱“兩會好聲音”,值得贊賞。
那么,學前教育到底該不該、能不能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呢?“兩會好聲音”該怎樣落實呢?
首先,就經費而言,這真的不會是一個問題么?如賀優琳代表所言,當年我國GDP總量不到10萬億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現在GDP總量67.7萬億,多做三年義務教育不行嗎?而姚愛興、朱玉華兩位委員則提議在寧夏先行開展試點實行免費學前教育,“以目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完全有能力在寧夏先行開展試點實行免費學前教育,提高學前教育普及程度,保障所有兒童,特別是農村兒童、貧困家庭兒童等弱勢兒童平等享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那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寧夏,尚且有實行免費學前教育的底氣,更何況其他地區乎?“這事不差錢,只差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關鍵在于政府真要能籌出足夠的錢,要有擔當和長遠考慮。
但是,學前教育能不能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兩會好聲音”如何才能真正落地,還必須正視諸多其他現實的困難,還要進行科學的考量。
2010年之前,學前教育一直都相當于“沒奶的孩子”。數據顯示,至2010年底,學前教育的政府投入僅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1.3%,發達國家是10%,甚至連非洲國家都有3.8%!毫不夸張地說,由于中央政府對學前教育幾乎沒有投入,地方政府的投入多具象征性質,我們欠學前教育的賬太多了!教育資源短缺,經費投入不足,師資隊伍不健全,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
一時之間,真的很難彌補眾多短板。設備等硬件或許還可以通過加大投入得以緩解,最為核心的師資隊伍問題,怎能在短期內有效提升?這幾年,令人觸目驚心的形形色色的幼師虐童案的頻發,便是我們當初漠視學前教育所釀下的苦酒。
此外,如果是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還必須考慮到義務教育的普及性、強制性。如果要普及,就意味著教學標準、課程標準等方面的相對統一。對于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學齡前兒童,這種整齊劃一的要求,是否會產生扼殺孩子天性和個性的負面作用,或許值得斟酌。
同樣,義務教育還意味著幼兒必須送到幼兒園就讀,這樣的要求是否妥當,也值得商榷。事實上,學齡前兒童是否進入幼兒園學習,完全可以因人而異,有條件的家庭,可以晚些入學,多一些父母的陪伴呵護,對孩子的成長或許更有利。如果強制要求幼兒離開父母,這不僅存在剝奪家長陪伴孩子權利的嫌疑,更會對幼兒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正是基于這些考慮,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在學前教育階段普及義務教育。英國固然將學前教育作為義務教育的一個階段,但主要體現為免費教育;芬蘭為6-7歲的學齡前兒童提供為期一年的免費學前教育,前提是家長自愿接受;200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曾就是否讓所有4歲的孩子接受學前義務教育進行投票,結果被民眾否決。
因此,與其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倒不如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更為穩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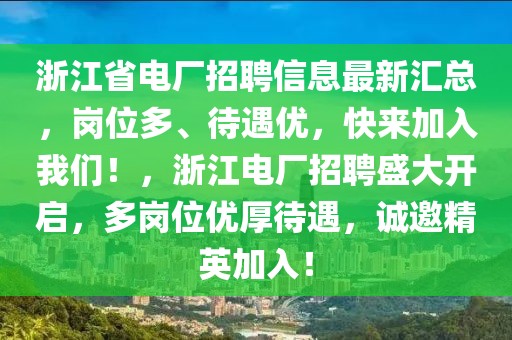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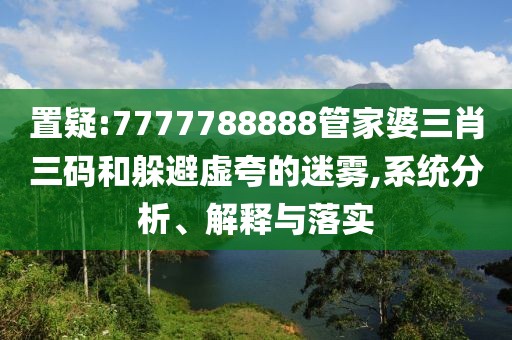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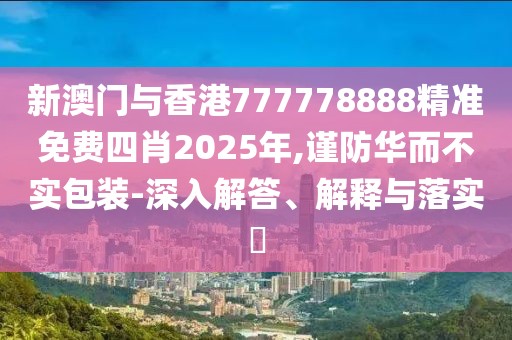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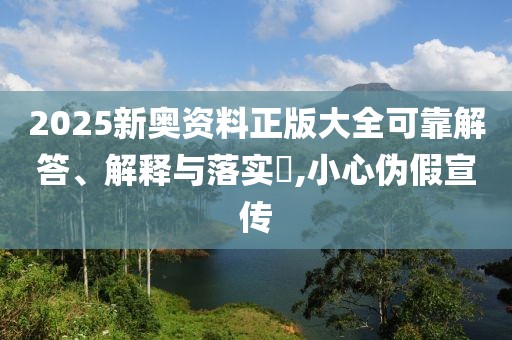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