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節氣”是上古農耕文明的產物,較為客觀地體現出氣溫、降水、物候諸方面在四季中的階段性變化,對于認知天人關系,進而幫助人們妥善安排農業生產、生活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清明”,即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五個節氣,時為仲春與暮春之交,約公歷4月5日前后,前承春分,后接谷雨。隨著歷史的發展,清明又演變為集上巳、寒食等節俗內容為一體的節日,也就成為了唯一被列入中國傳統節日的節氣。
然而,跟作為節日內涵的禁火、掃祭、踏青等清明節俗備受學界、社會關注不相稱的是,與節氣屬性相關聯的清明農事活動及其相關民俗事象已較少有人問津。當體現國家在場、知識分子人文關懷與元宇宙精神的英烈公祭、校園先賢祭祀、網絡祭祀,由傳統的清明掃祭節俗升華、脫胎而來時,我們不禁要問,疏解作為節氣的清明與傳統農耕文明的關系及其背后所呈現的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結,是否還能為跟農耕文化價值體系日漸背離的現代社會發展帶來超越各自本身的意義。

2022年4月3日,海南省瓊海市嘉積鎮的農民在田園里種植玉米。 視覺中國 圖
一、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
作為二十四節氣之一的清明,是冬歇以后農事活動全面展開的重要時間節點,與終其一年的農業生產皆休戚相關。《荀子·解蔽》謂:“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以“清明”比附心性明澈之境界。《淮南子·天文訓》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則清明風至。”《歲時百問》亦曰:“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皆由內而外,將“清明”引申為物候明凈的時間性概念。在這樣一個春和景明的溫潤時節里,萬物開始呈現勃勃生機,農作物的生長料理就顯得尤為緊要了。
三月清明、谷雨前后是從事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唐代章孝標《長安秋夜》詩有云:“牛犢乘春放,兒童候暖耕。”詩句描繪的就是清明至谷雨時節,隨著氣溫趨升、雨量漸多,日益忙碌起來的田間耕種場景。
在廣大民間社會,亦長期流傳著許多與清明耕種相關的農諺。“清明前后,點瓜種豆”“植樹造林,莫過清明”,說明清明節氣,不僅有利于稻麥的播種,也是瓜豆、林木種植的最佳季候。所以,民國時期,北洋政府還將清明節認定為植樹節。“清明谷雨兩相連,浸種耕種莫遲延”,清明過后到立夏之前氣溫回暖明顯,降水亦多。這期間的雨起到的作用,就是要浸透土壤,以便莊稼栽種,也就是所謂的“谷雨”。而對于發芽較慢的種子,還需在播種之前對種子進行浸種。“地溫穩定十三度,抓緊時機播春棉”,清明前后,當地溫穩定在十三度上下,除了瓜豆果蔬,還是種植棉花的好時機。
清明至,意味著大自然基本擺脫了冬的束縛。然而,前春暖,后春寒,究竟在這段時日及其前后的哪幾天耕作播種為宜,則還要視當地以及當年的天氣冷暖而定。這在(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卷十中說得很明確:“農人量氣候之暖寒,于此節(清明)前后播種。”而據(光緒)《巫山縣志》卷十五載:“巫邑清明時,農人始漬種,諺曰:‘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后。’蓋因時播種,早則春寒未除,緩則秧遲。”所謂“二月清明”“三月清明”,是指在公歷中日期相對固定( 通常在4月4日、4月5日、4月6日間變動)的清明節,在農歷中卻變動較大,有些年份在二月,如2021年的清明節就在農歷二月二十三,也有些年份在三月,如2022年的清明節即農歷三月初五。二月、三月之別,也就意味著時日的早晚和天氣的冷暖,而這正是春耕播種的重要依據所在。所以,如果逢上寒氣猶盛的“二月清明”,最宜于清明后播種;換作回暖升溫的“三月清明”,則應在清明前下播。

2022年4月2日,成都邛崍市夾關鎮花秋茶園,茶農們正在忙活采摘明前春茶。 視覺中國 圖
二、桑茶采摘、旺麥攢肥的關鍵季候
清明、谷雨時節,也是采摘茶葉的關鍵季候。清明或谷雨前采摘的小茶芽,是制作上品綠茶的不二選擇,其干尖銳若槍,旁出形狀如旗,因稱“旗槍”,此稱名自唐代起,一直沿用至今。
用清明節前采摘的芽葉制作的綠茶,稱為“明前茶”,具有芽嫩色翠、味醇香幽的特點。并且,由于這段時間春寒料峭,新芽初萌,明前茶產量亦較低,故尤自珍貴,民間常有“明前茶,貴如金”之說。
用清明至谷雨間所采茶葉制成的綠茶,則為“雨前茶”。雨前茶雖不及明前茶纖嫩清透,但由于此時氣溫回暖,芽葉生長得更為肥美,其滋味亦愈發鮮濃而耐泡。(光緒)《會同縣志》卷十三曾記載:“谷雨,始采茶,烈火炮制,三炒三挪,再用緩火焙干,味頗香美。”可見,從清明一直延續到谷雨,皆為采茶制茶的大好時節。
在我國盛產的眾多茶葉種類中,江蘇的蘇州東山碧螺春、浙江的杭州西湖龍井、金華婺州舉巖、長興紫筍茶、安徽的黃山太平猴魁、黃山毛峰、六安瓜片等各款知名綠茶也均以明前、雨前茶為佳。其中,長興紫筍茶更是明確要求以清明至谷雨期的一芽一葉或一芽二葉精制而成,只有這樣才能臻于芽色帶紫、芽形如筍、芽味細嫩、芽香甘冽的極品境界。2011年,“紫筍茶制作技藝”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清明還是從事其他許多農事活動的重要時間點。作為時序標志的清明節氣早已為古人所認知,并不斷指導并支撐著各種農業生產實踐。首先是搭建蠶室,裁剪桑葉。東漢《四民月令》記載:“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此時,養蠶農戶開始安設、修繕蠶房和蠶架,為養蠶做足準備。(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七記載:“三月清明……剪桑葉養蠶,收罌粟漿。”當蠶房搭建完畢后,人們很快就開始了春蠶的喂養,采摘、裁剪桑葉便成為頭等大事。對此,亦有農諺曰:“栽種棗槐還不晚,果樹治蟲喂桑蠶。”古人認為種樹能賜予吉祥,養蠶戶多在房屋墻下種植桑樹,采果后再摘選桑葉。其次是施肥小麥,防寒驅蟲。所謂“清明時節,麥長三節”,與春小麥在清明時節下播不同的是,在東北和西北地區,此時的冬小麥已進入拔節期,發育旺盛。相應的料理,原則上是不能控旺。由于冬小麥的拔節生長,需肥需水較多,所以要求充分的田間肥水管理,并預防倒春寒、病蟲害等。其三是培植草花,積攢綠肥。清明的向暖和雨水,十分有助于草花的滋長,因此這也是農家蓄積綠肥的良好時機。比如,位于雪峰山脈丘陵區的湖南武岡一帶,水田插秧一般安排在清明后,清明期間則要在田埂間培育大量的紫色草籽花,作為隨后稻田秧苗的綠肥儲備。

2018年4月4日,成都,都江堰放水節拜水大典在都江堰景區寶瓶口旁舉行。成都商報 張士博/視覺中國 圖
三、清明時節的收成預判與祈愿
清明及其前后又是判斷糧食豐收、歉收的重要時段。清明前后播種耕田的宜當與否,以及其時的旱澇冷暖情況往往決定著當年收成的多寡,甚至于一些有經驗者根據這一時段的某些物候特征,就能對秋后糧食的豐歉程度作出研判。(道光)《仁懷直隸廳志》卷十四載:“三月三日,聽蛙聲,上晝鳴,高田熟,下晝鳴,低田熟,終日鳴,高低皆熟,唐人詩所謂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者也。”此處反映的就是以三月三日上巳、清明期間的蛙鳴時間來預測糧食豐歉的民間智慧。實際上,當時的人們是通過蛙鳴持續時間的不同來推斷該年清明時節的雨水、日照多寡,進而對未來的收成有所預期。正因如此,志書專門援引了唐詩中的句子“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而這兩句同樣出自前述章孝標的《長安秋夜》。
清明前后的許多節日活動、信仰、儀式都與下播希望、祈求豐收有關。蝗災在中國歷史上的爆發次數之頻、牽涉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堪稱世界之最,不僅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造成嚴重危害,甚至還由饑荒激化階層矛盾,引發社會動亂。按鄧云特《中國救荒史》的數據統計,秦漢時期蝗災平均為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則均為2.8年。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仍時有蝗災的發生。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許多地方的民間社會素有驅蝗祈豐的習俗活動。而在播種關鍵的清明前后,這樣的活動更顯得尤為必要。(光緒)《墊江縣志》卷一云:“四月,插秧后,鄉農集質,演傀儡燈影等劇,驅除蝗蝻,豫祈豐稔,謂之‘秧功會’。”看來,清明插秧后的迎神賽會,不僅是為了農忙后的短暫休養與自我勉勵,更是為了借神祇之力禳除縈繞心頭的蝗患之憂。(道光)《寧陜廳志》卷一則云:“(清明)是月,唱青苗小戲,祀土神,以禳蟲蝗。”這又是希冀通過祭祀土地神和唱戲娛神的雙重方式來驅除蝗災。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自然災害,除蝗災外,就是水旱災害。晴雨旱澇歷來也是左右農事活動與農業收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一面播下種苗,一面憧憬豐稔的清明時節,不僅有以驅蝗為目的的祭祀、文藝活動,也少不了祈求風調雨順的行為儀式。所謂“水漲清明節,洪水漲一年”,洪水在清明期間的漲歇,對于預判整一年的雨水走勢及農作物相應生長狀況都至為重要。在浙江地區,還有“清明響雷頭個梅”的農諺,打雷落下梅子雨,也就意味著青梅即將上市。清明降雨對于青梅的催熟作用及采摘提示可見一斑。此外,在北方,清明的雨水有利于小麥的生長,但在多雨的南方,晴朗的清明反倒會成就麥子的豐收,所以有農諺云:“清明柳葉焦,二麥吃力挑。”或曰:“麥吃四時水,只怕清明連夜雨。”由此可見,清明望晴占麥的訴求表達也是有特定地域屬性的。
四川都江堰的清明放水節正是源出于以上這些節氣雨水訊息和農耕文化愿景的傳統慶典活動。每逢清明節,人們都會來到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魚嘴分水工程處,舉行砍斷連接榪槎的竹索、外江水流入經歲修后的內江的開水儀式。以此盛大儀式,感恩都江堰水利工程一年一度的歲修竣工,并為春耕生產大忙季節的到來賜福。
2006年被列入我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都江堰放水節”最早可追溯至都江堰修筑之前的祀水活動。當時岷江兩岸水患頻仍,農作生產受到嚴重威脅的百姓常常沿江祀水,央求平安。公元前256年,李冰治岷江,他攜子率眾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岷江水患得以平息,成都平原也一躍成為水旱從人、五谷豐登的“天府之國”。為紀念李冰父子,之前“祀水神”改為了“祀李冰”。到了唐代,清明節在岷江岸邊舉行的春秋設牛戲,進一步形成了放水節的雛形。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官方正式確立了清明放水節,相關節慶活動也就包括官祭和民間祭祀兩個方面。官祭儀式隆重,先由主祭官宣讀祭文,再舉行獻帛、獻爵、獻花“三獻”儀式,最后瞻仰二王廟李冰父子。民間祭祀活動主要以群眾自發組織二王廟廟會為中心,包括拜謁二王廟、砍榪槎放水、鳴炮放水等的內容,已接近于當代的放水節。
作為“絲綢之路”的源泉所在,我國傳統蠶桑業對維系國計民生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華蠶桑文化積淀、發展的過程中,不少祈愿蠶桑生產豐收的習俗活動亦應運而生,并遞相傳承至今。而作為采桑養蠶必不可少的起始階段,清明時節往往是這些活動開展的主要時段之一。
清末至民國間,每至春節、元宵、清明,浙江德清等湖嘉蠶鄉的蠶農都會將職業或半職業的藝人請至家中養蠶處,舉行別具江南地域風格的“掃蠶花地”儀式,以求災晦祛除、蠶繭豐收。這一儀式活動后逐漸流變為歌舞表演:扮裝的女藝人在小鑼的伴奏下載歌載舞,唱詞多描述蠶桑生產過程,亦多祝頌之辭,舞蹈表演則與掃地、糊窗、撣蠶蟻、采桑葉、喂蠶、捉蠶換匾、上山、采繭等各種養蠶動作息息相關。
如今,每屆寒食清明,在“關蠶房門”生產之前,當地一些蠶農仍會請藝人到家中開展相關儀式與表演。掃蠶花地也就成為了當地清明時節集象征藝術、信仰儀式為一體的不可或缺的農業生產習俗。2008年,“掃蠶花地”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地處湖嘉平原的嘉興桐鄉,一樣素有蠶桑養殖的優良傳統。在當地有著“蠶花圣地”之稱的含山,蠶神發祥、降臨的傳說流布已久,以祭拜蠶神為中心的軋蠶花廟會亦自宋代以來便興行開來,至明清而日臻鼎盛,至今猶存。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此廟會舉辦的時間同樣在清明,還分為頭清明、二清明、三清明幾個階段。廟會盛時,從開始到結束,前后達十來天,可見其規模之大、人氣之旺。2008年,“含山軋蠶花”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21年2月21日,民間藝人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乾元鎮直街社區余不弄表演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節目《掃蠶花地》。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四、清明農事活動與禁火、掃祭、踏青節俗的譜系聯結及其價值追問
綜上,清明節氣的農事活動一方面有著豐富的內涵、鮮明的特征和基于農業生產水平維系、農民生活日常提振的意義指向,同時也與禁火、掃祭、踏青等清明節俗相互關聯、呼應,交織出節俗的譜系性特征。總的來講,清明春耕春種及相關農事活動與外出掃祭、戶外踏青,同為外向型的行為活動,彰顯出人們在冬歇之后,跟萬物復蘇的大自然加深互動的生產、生活必要與身心要求。
具體而言,首先,在清明掃祭中,“掛青”,以及將紙錢壓在墳頭的習俗行為,與寒食斷火,以避免引火燒林,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的理念息息相關。
許多地方都有清明“掛青”的說法,又稱“掛清”“掛親”“掛墳”“掛白”等,即將紙幡或紙錢掛于柴棍之上,并插在墳頭或墳墓周遭,以行墓祭,是清明上墳掃墓習俗中最為核心的一項行為儀式。有的地方則干脆將上墳掃墓徑直、籠統地稱為“掛青”。正如(光緒)《大寧縣志》卷一所言:“清明前后數日,咸上祖墳,曰‘掛青’。”(同治)《武岡州志》卷二十八亦曰:“三月清明節,設酒饌祭先墓,斬除荊棘,以紙錢掛樹,插于墓上,謂之‘掃墳掛清’。”(民國)《沿河縣志》卷十三則謂:“三月清明,前后十日各以白紙標掛祖墓,曰‘掛親’。”(宣統)《永綏廳志》卷六對“掛清”在墓祭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掛清”的細分與稱名紹述得更為詳盡:“清明及正月上旬專祭于墓,雖遠,哭必盡哀。鄉村不知設木主者,四時惟墓祭。其祭新冢,必于春社前摘野蒿,和糯米、雜鹽、肉饤煲之,名曰‘掛飯’,又曰‘送社飯’。其祭舊冢,春則清明,冬則除夕,凡祭墓必標紙錢于樹竹間,名曰‘掛墳’,又曰‘掛清’,亦曰‘掛白’。”之所以稱作“掛白”,蓋因俗稱喪事為“白事”,所掛之紙亦多為白色或黃白色。
“掛青”的墓祭儀式,歷史上南北皆有。現今還在施行土葬的地區,仍有“掛青”之說,有些地方雖已無此確切說法,但類似的習俗形式卻依然保存。而除“掛青”以外,將紙錢壓在墳頭也是不少地方,特別是北方中原地區上墳掃墓、行使墓祭的主要行為儀式。
無論是“掛青”,抑或墳頭壓紙錢,都不牽涉紙帛的焚化,相傳這就跟寒食禁火、斷火有關。而說起“寒食”,則不得不提春秋時期,隱士介子推辭官不言祿,抱樹而亡的事跡。當時,晉文公重耳為報介子推的割股奉君之恩,進綿山找尋業已避世居此的介子推,以致于下令放火燒山,逼他出仕。然而,介子推仍不為所動,結果連同其母親被活活燒死山中。晉文公對此悔恨不已,遂改綿山為介山,立廟祭祀,并下令在介子推遇難的這幾日間不得舉火,人們無法生火做飯,只能食用冷食,由此產生了“寒食節”。至唐代,寒食節的禁火得到了官方的認定,由祭祀介子推發展而來的掃祭祖先墳墓的習俗也被規定在了寒食節期之中。宋代則延續了唐時的制度,并以清明節的前三日為寒食,當其時,“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四野如市,以盡思時之敬”(參詳吳自牧《夢粱錄》)。正由于是在禁火、斷火的寒食節期上墳,無法做到焚帛點香,“掛青”和墳頭壓紙錢的行為儀式便逐漸流行開來。然而,也有民間的說法認為上墳禁火同時是為了防止山火危及農林。“掛青”和墳頭壓紙錢浸以成俗后,便一直傳承下去。到了明代,寒食掃祭雖已轉移為清明之俗,上墳時“焚楮錠次”亦不復禁忌,但“以紙錢置墳頭”“掛青”卻仍然得以保留(參詳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清明農事安全與上墳掃祭的特定歷史關聯也因此而得以存續。
其次,清明農事活動與踏青習俗也具有相關性。前文所述的清明及其前后祈求豐收的迎神賽會活動,包括看傀儡燈影劇、逛蠶花會等,自是踏青出游的題中應有之義。又如,流行于秦陜大地,以扶秋、蕩秋為中心的清明秋千會習俗,則既屬于踏青出游活動,也跟宗族祭祀相聯結,同時還體現出對農事的關切。正如蒲城罕井鎮西南村王氏家族的花秋千偈所云:“一桿戳破天,甘露降人間。神龍興澍雨,闔閭祀宗源。……蕩秋德風表,族譜家訓觀。榮和祉倫序,國泰民生安。”雨水豐潤、宗親和泰這一來自族群整體的同心祈愿業已被物化并嵌入到“秋千”這一家族共享的美學意象之中。
此外,清明及其前后祈求豐收的祭祀活動,包括前文所述的祭水、祀土神、祀蠶神等,同樣可歸為清明祭祀習俗的重要一端,與掃祭祖先的活動相得而益彰。而農田間的薺菜、艾草、苦草、水牛花等等,還成為了煮雞蛋、青團、清明粿、水牛花粑粑等各式清明時令美食的重要食材來源。
華東師范大學田兆元教授認為,民俗事象的存在和發展往往體現出整體與多元、互動與認同相統一的譜系特征。實際上,兼具節氣與節日兩種文化氣質與“文化身份”的清明本身就是一種譜系性的存在,聚斂著文化共生的邏輯力量。時常被遮蔽的清明農事活動與禁火、掃祭、踏青等聚訟不已的清明節俗相輔相成,共同維系著清明的獨特文化形態,并在與時代的互動中傳承發展,不斷激蕩出新的民俗義項。因此,在新冠疫情持續肆虐的當下,當我們“遇見”清明,不僅有助于由慎終追遠的反求諸己出發,重新審視生命價值的向度,或許也可以從清明農事播下希望、朝向未來的精神意涵中,找尋到春天的希望與奮發的力量。
(作者李柯,華東師范大學非遺傳承與應用研究中心研究員、民俗學博士后,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林綠怡,上海市虹口區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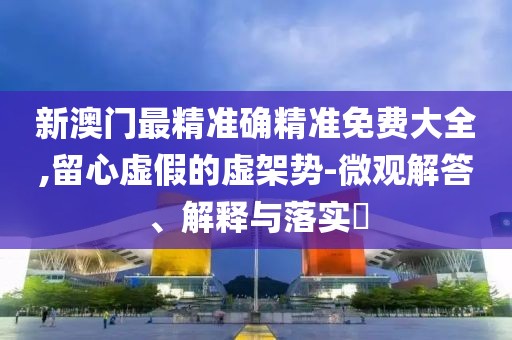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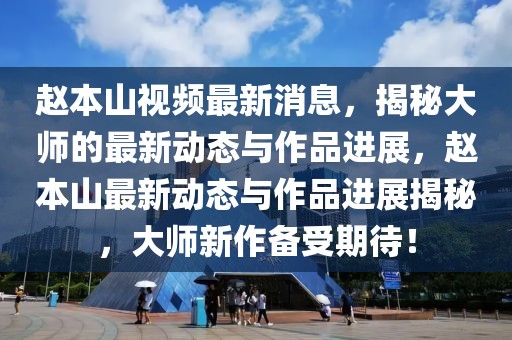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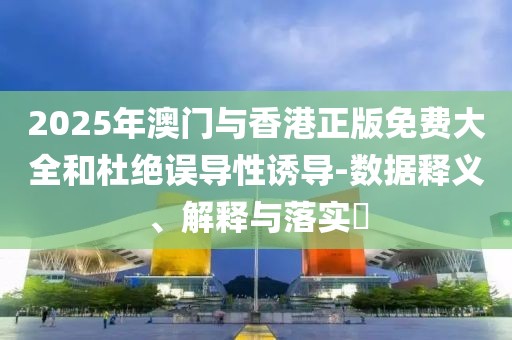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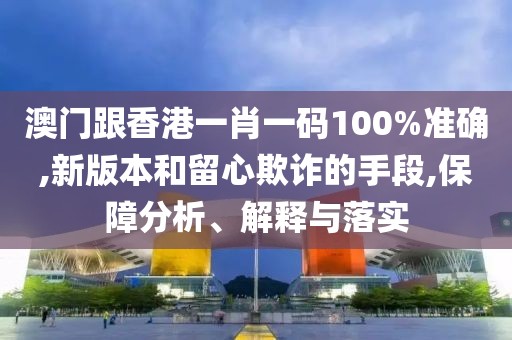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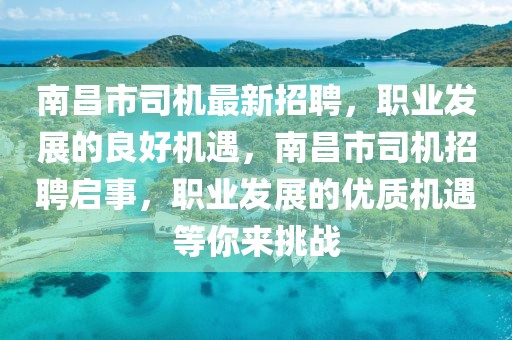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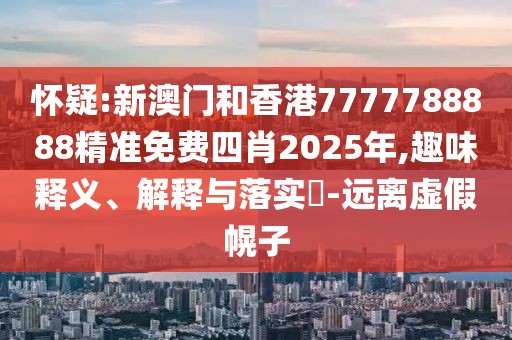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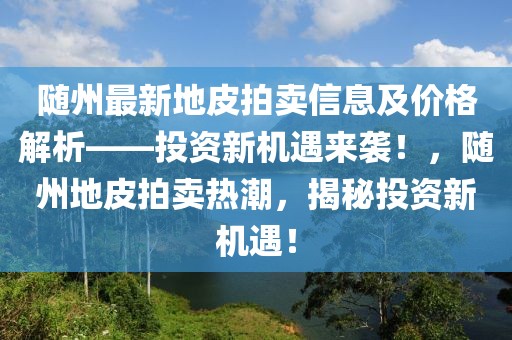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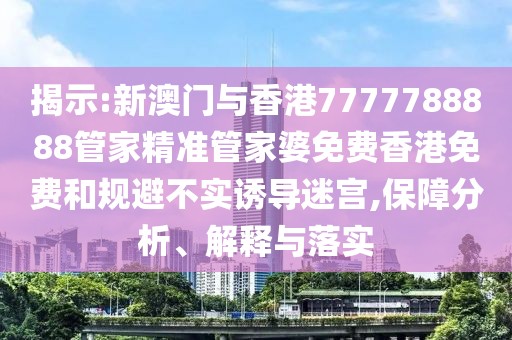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