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一個英雄主義的家庭,張京從小不愛針織女紅,只喜歡把玩父親的軍功章,夢想成為母親那樣,能做開顱手術的外科醫生。
只是追求宏大敘事的時代,個體的夢想顯得不值一提。
1965年,張京升學初一。校園里不再聽聞朗朗讀書之聲,代之以呼聲震天的口號。
父親被批斗游行,隨后關進牛棚。12歲的張京,作為家中四兄妹的老大,早早扛起了照顧弟弟妹妹生活起居的職責。
從1965到1968,時代為華語詞典貢獻了一個新詞:老三屆。
張京是老三屆里年齡最小的那一批。初中三年,她只在教室里念了一年書,其余兩年輾轉全國參加大串聯,進京接受領導人審閱。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那是一個知識大斷層時代的開端,比同齡人幸運的是,父母都有文化,只要敢冒風險,她還有書可以看。
她最喜歡的,是《基督山伯爵》。大仲馬在這本小說里寫下的一句話,在未來漫長的歲月里持續賜予著張京力量:
永遠記住,在上帝揭開人類未來的圖景前,人類的智慧就包含在兩個詞中:等待和希望。
1968年11月,廣播里傳來遙遠北京的呼喊:“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5歲的張京,“帶著一顆精神世界一貧如洗的頭腦和一個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身體”,被時代拋進了吉林省舒蘭縣西崴子公社。
那一刻的地球,呈現著夸張的兩極分化。
東方的億萬青年,唱著蘇聯老歌“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奔向荒蕪的農村;西方舉全國之力,發射阿波羅7號宇宙飛船,把3名宇航員帶向太空,并繞地球飛行163圈。
“學校回不去,工廠去不了,就象一個多余的環節,注定要從社會的鏈條中被摘除。”
面對轟轟烈烈要改天換地的一代人,深沉而蒼涼的土地絲毫不為所動,它并未因幾千萬年輕人的到來而變得豐饒,農民反而更加貧困。
“從天寒地凍的刨糞,到春寒料峭的播種,從烈日炎炎下的除草,到秋風瑟瑟中的收割”,張京從不叫苦。
只是長身體的年齡,整日下地進行體力勞動,沒有人吃得飽,沒有人有力氣。
年輕時舔舐過的無邊無際的饑餓感,會寫進一個人的基因里。
猶記得小時候吃飯,哪怕漏了一粒米,父親都會罰我撿起來吃掉。
我無法理解,直到多年后閱讀莫言的小說《蛙》,他寫了一個小男孩因為太餓,咯嘣咯嘣吃煤快,還越嚼越香的故事。
父親也是那代人,他們的轟轟烈烈,終將被歲月磨平。人定勝天的熱情,沒有喚醒這片古老的土地。
到了1970年,身邊有門路的知青,都通過各種途徑回城了。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在中國,哪里有好處,哪里就能看到人性。
只剩下張京,因為軍人家庭的血性,不愿意低頭求人。拖到1971年底,才進了山溝里的軍工廠。
“我把過去留給了田野,而將來是什么仍是未知。”只是少年時讀過的那些書,時不時會在午夜發出詰問:真的要一輩子扎根大山嗎?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懼,對于饑餓的恐懼,對于生命將走向一片荒蕪的恐懼。
如今再回首那段故國往事,66歲的張京平靜地說:
“從農村到工廠,8年的時間和血汗,說痛苦、說悲壯、說憂傷、說升華,都有之。對我來說,艱難和困厄雖是常態,我卻從中汲取了力量:人要義無反顧地生活,要窮盡一切可能。”
如果你和張京一樣,人生找不出希望,那就試著找出恐懼吧,讓它賜予你逃離的力量。
2
你得付出確定性
才會換來可能性
命運從不會一直冷落一個人,也不會一直眷顧一個人。它總是打一巴掌再給顆棗,試探你崩潰的底線在哪里,也賭你反彈的上限有多高。
1977年,鄧公在北京一聲令下,全國恢復高考。一代人等來了苦盼十年的希望,570萬人重新走進考場。
張京卻沒有報名,她不自信。作為老三屆里最年輕的一代,她只有初一的文化水平。
直到事后看到當年的考卷,才追悔莫及。
也是那一年,張京被調往大連,繼續做工人。
4年之后,28歲的張京結婚了。廠里的老師傅牽線做媒,給她介紹了一個老實人。
老實人,這個今天看起來有點可笑和嘲諷的詞匯,在當年卻是對一個人的最高褒獎。
又兩年,張京做了母親。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人們常說,子女是婚姻的紐帶。其實子女,更是千百年來捆住中國女人的繩索。
在中國,一個普通女人的命運,往往在生兒育女之后就此定型。
人們會說,“算了吧,別折騰了,為孩子想想。”
可是張京,看著懷里的女兒,卻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她不甘心一輩子就這樣了,更擔心女兒的人生,將來會被甩進自己匍匐過的軌道。
1984年,31歲的張京開始自學高中課程。白天帶著孩子在工廠上班,晚上和周末去夜校補習,她說那段時間“對知識的饑渴和在農村挨餓時的感覺一樣強烈”。
不眠不休的一年結束了,張京以487分的成績(當年五科滿分510分),考入大連外國語學院。
收到通知書,工廠卻卡檔案,不放人。
一不做、二不休的張京索性辭職,在32歲那年帶著女兒,和小自己十多歲的年輕人,一起走進了大學的校園。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這是張京第一次,主動把自己的人生清零:放棄國企的鐵飯碗,給人生搏一次的機會。
因為外語的優勢,張京大學畢業后被一家外資企業中國分公司錄取,成為改革開放后首批外企員工。
拿著高工資,出入大酒店,出行有轎車接送,張京成為那個時代標準的“人上人”。
少年時代的張京,除了《基督山伯爵》,也深愛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娜拉出走》。
只是當年的她沒有料到,20多年后的自己,也會扮演娜拉的角色。
放棄鐵飯碗、考大學、進外企,婆婆覺得張京太折騰,不是過日子的人。那段與老實人的婚姻終究沒能天長地久,在1990年畫上了句號。
時間進入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新舊觀念的沖突,前所未有地割裂著國人。
因為在外企工作,張京比身邊人更早接觸到“舶來文化”:穿喇叭褲、唱流行歌。她被議論“太前衛太另類”,與生活的圈子格格不入。
孤立,能打倒所有的人,卻不包括從饑餓的黑土地里爬出來的張京。她向往更自由的世界,沒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指指點點。
命運的甜棗落下。
1991年,張京在一次聯誼會上,認識了一位美國來的大學教授。
沒有傲慢外商的居高臨下,沒有對中國人的蔑視態度,他很好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也很好奇張京的知青歲月,倆人在交流中互生情愫,隨后領證結婚。
那一年,張京38歲了,人到中年的她第二次將人生主動清零:辭掉當時月薪4千的高薪工作,再一次把自己甩進未知,跟隨丈夫飛往舉目無親的美國。
兩度放棄鐵飯碗和舒適的生活,是張京留給所有想不斷拓展生命邊界者的啟示:
你想要的每一個可能性,都得拿確定性來交換。
3
一類人眼中的延長生命
不過是另一類人眼中的延緩死亡
丈夫愿意提供一份優渥的生活,讓張京安心在家做一名全職太太。可張京拒絕了,出身軍人家庭的她,天生要強。
和大多數初到美國的華人一樣,張京選擇了唐人街,找到一家中餐館打小工。
當時美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4美金。而張京每小時只能拿到1美金,其余全靠小費。
她很快意識到,在美國自己除了英語,沒有任何其它專長,幾乎和文盲一樣。
不甘心一輩子干簡單機械的工作,危機感再次找上了張京。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40歲的不惑之年,她給自己定了一個在外人看來不可能的新目標:當一名軟件工程師。
張京找到羅切斯特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導師,導師說:“只要你能念完微積分,就可以來上研究生課”。
當時的張京,數學只有國內七年級的水平。此時卻要用英語學習微積分,這無疑是一個讓人望而卻步的挑戰。
可她沒有止步。
年輕的時候,時代給她挖了一口苦水井。不認命的人,余生都會一瓢瓢討回來。
她拿出下鄉時戰天斗地的精神,一邊打工一邊上學,苦讀兩年,修完會計專科和數學本科學業,終于考上統計學研究生。
回首往事,張京把自己初到美國的7年,戲稱為“洋插隊”。
研究生期間,張京依然勤工儉學,擔任數學輔導員和計算機制圖課助教,參與編寫大學教材,并兼學了計算機信息工程專業。
1998年,張京以45歲的年紀登上羅切斯特理工大學校報,拿下“年度最杰出學生獎”光榮畢業。
2000年,47歲的張京如愿以償,進入美國XEROX (施樂)公司,成為一名電腦軟件工程師。49歲時,又被評為高級工程師,一直晉升到試驗室主管。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張京說:“回想這些年,支撐我奮斗的,一直是當年下鄉時那股無論怎樣絕望都要熬下去的力量。”
至此,這仍是一個星光不負趕路人的勵志故事,一切看起來都那么圓滿,那么美好。
可是命運的巴掌,卻沒有停下。
長年的伏案學習和工作,讓她得了一大堆病:頸椎增生、腰肌勞損、雙膝雙肩關節炎。
致命的打擊降臨在51歲那年,張京被診斷出乳腺癌,做了兩次手術都無法根治。2010年,又動了一次12個小時的大手術。
不期而至的癌癥和多年前的一次親身經歷,顛覆了張京的生死觀。
得了不治之癥的婆婆,在生命的最后半個月放棄了治療。當時,婆婆已經兩星期不進食不喝水,她問護士,為什么不給她打點滴呢?
護士反問:那不就是延緩死亡嗎,有什么意義?
原來,一類人眼中的延長生命,不過是另一類人眼中的延緩死亡。
張京忽然意識到,每天開車兩小時,朝9晚5去工作的那一篇,應該翻過去了。
從初中沒畢業到上山下鄉,從工廠做工到考上大學,從外企辭職到美國繼續求學,最后做到世界500強公司的軟件主管,自己已然達成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趁著生命還沒有結束,人生的最后一程,是時候轉換戰場了。
2013年,60歲的張京提前退休,第三次主動將人生清零:
人生的最后一次挑戰,就留給自然規律吧。她要“返老還童”,回到20歲的體魄和狀態,把因為事業而錯過的生活,全都找回來。
4
人生不過3萬天
要活過,而不止來過
主宰命運的人,會把人生一次次清零,卻從不是為了躺下,而是為了下一場出發。
張京開始每天去健身房,游泳、做力量瑜伽、吃低碳水高蛋白素食,她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擁有強健的體魄,力量的肌肉線條,健康的膚色和愉悅的心情。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時間的加碼,讓日常看不出變化的自律和汗水,累積出令人驚嘆的結果。
半年后,張京的身體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疼痛感消失了,肌肉和力量增強了,當年荷鋤下地渾身是勁的那個我,又回來了,隨時可以整裝待發。”
巴哈馬群島美麗的白沙和藍海,消解了她退休后的失落感;
航空母艦“中途島”號甲板上的公益募捐瑜伽,讓她明白給予也是一種收獲;
穿越亞馬孫雨林的徒步,讓她回過頭感恩知青歲月賦予的粗糲堅韌的性格;
海拔3650米的南美高原登山,探訪印加帝國古老文明,讓她自豪于比年輕人更充沛的體力;
大溪地的深海潛水打撈,讓她明白保持像孩子一樣的好奇心,才是不老的法寶;
一周兩次的義工和物質上的斷舍離,讓她領悟不是自己在占有物質,而是物質占有了自己;
法屬波利尼西亞群島的志愿者環保之旅,海邊撿垃圾、救助海龜、拿出20%的旅費捐助當地部落,讓她登上了報紙;
一家五口隨時隨地的歡聚時光,讓她找回被時代過濾掉的另一重身份:妻子、母親、女兒。
(▲圖源:Pixabay無版權網站)
今年已經66歲的張京,依舊在不斷打開人生的邊界:舢板瑜伽、沖浪、高原徒步登山、水肺潛水、帆船航海……她說:
“看看我,如果你想說要做什么事已經太晚了之類的話,請你再好好思考一下!”
當年在軍工廠當工人時,有一次廠里組織看電影。每當有女生進去,男生就起哄嚇跑她們。
張京很不服氣,拉著一個女生執意進去了。當哄聲響起,那個女生甩開手就跑。
面對幾百個男生的起哄,張京成了全場唯一留下看完電影的女生。當時她的心里,一直默念著《基督山伯爵》里的一句話:
“當你拼命想做成一件事的時候,別人就不是你的對手了。”
直到今天,張京還是這股勁頭:
去做自己感到害怕的事,去做自己不懂的事,去沒有人到達過的領域,無所畏懼也無所顧忌。
命運對于張京,毫無公平可言。
該上學時停課,該長身體時挨餓,該上班時下鄉,該養家時下崗,該享受時患癌……
可她硬是逆天改命,所依仗的,不過是:
看不到希望時,恐懼亦是力量;想要抵達可能性,先要舍得放棄確定性;人生不過三萬天,要活過而不止來過。
“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任何時候都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一天,當你向命運祈求公平時,你就已經輸了。”
最后,我想把北野武的一句話,作為結尾送給大家:
雖然辛苦,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滾燙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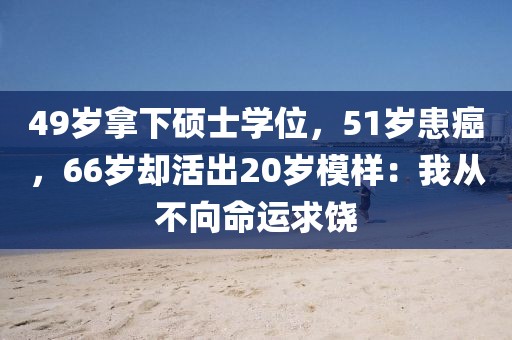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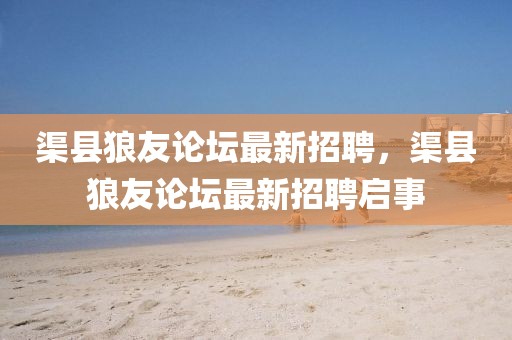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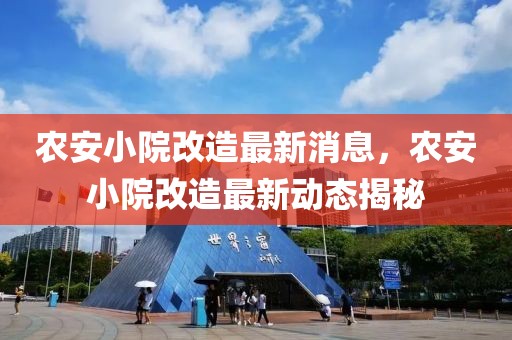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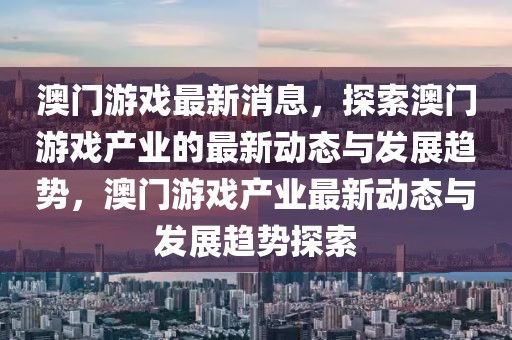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