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中國境內的國際都市,就繞不開上海和香港。
要說雙城記,上海和香港相距太遠,一個在長三角,一個是珠三角,地理上八桿子打不著,在省級區域經濟內沒什么競爭關系,和濟南對青島、成都對重慶、南京對蘇州完全不同。但在更大的地理視角下看,上海推動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定位,都與香港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
從發展路徑的角度來看,上海和香港更是繞不開的“雙城”。鴉片戰爭以后,兩個城市在同一時期開埠,其發展均受到中國內地大趨勢的推動,中國發展道路的變化從滬港雙城的演化就可以窺出一二要點。而要尋找他們未來的趨向,也必須首先回到歷史。
一、香港與上海的歷史性“同框”
在晚清專制君主官僚制彷徨之際,在近代歐風美雨的沖擊之下,香港和上海的一次重要的歷史性“同框”,改寫了這兩座城市的未來命運。
1842年,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要求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當時的英國人,為何要選擇一塊“卑濕之地”和邊陲小島作為通商口岸及割讓地?
1845年11月29日,蘇松太兵備道宮慕久與英國領事巴富爾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對于清朝官員而言,這塊地方在上海縣城之外,是荒蕪之地,除了少量農田,其余的都是“卑濕之地,溪澗縱橫”。
但英國人并不這么看,早在1842年,巴富爾過來考察時,就認為這塊地方“濱江、開闊,利于貿易”。具體來看,萬勇陳述巴富爾選中這一塊地方的三個好處:一是東靠黃浦江,北靠蘇州河,近鄰縣城,內可通過長江深入中國腹地,外可進出外洋與世界聯通;二是靠著黃浦江邊,航道寬,有充裕的海岸線建設碼頭,停泊商船,滿足貨運需求;三是江上有英國軍艦游弋,保護本國人的經商和居住安全。
萬勇,2016:《近代上海都市之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時,上海是江海聯運的中心,也是唯一一個可以江海聯運的城市。上海的這個區位意味著,在航空沒有取代海運之前,只要中國與世界的貿易連接不斷,中外貿易額越大,上海的地位就會越重要。彼時清朝和英國官員視角的差異,正在于此。
鴉片戰爭之后,英國僅僅將香港作為英國遠征軍的根據地和英國貿易機構的基地,而非貿易用途的通商口岸。這一要求,就意味著選址需要“港闊水深”。此外,當時鴉片貿易是英國人最看重的要素,由于主要通過廣州貿易,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就成為最佳方案。隨后香港的首任總督將香港定義為自由貿易港,以維多利亞港為中心建設香港,并作為基地發展其遠東的海上貿易。這些地理上的特征,讓香港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轉口貿易基地,并由此而催生船舶工業。
從地理上看,香港位于中國邊陲,是不折不扣的小漁村,并且這個地塊山多平地少(后來的很多繁華地塊都是填海而成)。在原有的內貿和農業生產主導的體系下,不可能有香港的發展空間。只有置身于國際貿易體系,香港的深水港及其與珠三角地區的連接,才使得香港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在鴉片戰爭前后,上海城市規模并不大,大約有20-30萬人,行政歸屬于松江府。據祁美琴的《清代榷關制度研究》,1795年各榷關的上報稅收顯示,上海的江海關僅有7萬多兩(庫平兩,下同),既遠不如對外貿易的粵海關(廣州)(117萬多兩),也不如內貿的蕪湖關(23萬多兩)。香港的基礎更差,在英國人眼中,它是一個“細小、荒蕪、不衛生、無價值”及“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為更不衛生”的地方。香港開埠時,港島上只有7450人。
鴉片戰爭后的50年,英國對香港和上海的治理有直接的影響,但表面上的權力架構并不相同。
上海是通商口岸,英國(及后來的法國、美國等)只能在上海租借土地,在租借的土地上,經清廷的批準,按西方的模式治理。隨后的制度演進,讓上海成為多國參與治理的租界地。1863年,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被稱為公共租界,統一由工部局(TheMunicipal Committee)管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徽章
工部局的權力幾經擴張,其執行部門涵蓋了商團、警務、衛生、教育等各個方面,還承擔市政建設、治安、征稅等行政事務,以及法院的部分職能,隨后其它城市的租界大多仿照上海成立了工部局。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獨一無二的實踐,成為一個共同公共管治的體系(曾經有人推動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并,但因法國政府的反對,最終在上海形成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兩個租界)。馬德斌教授認為,由于上海公共租界是共同管理的,因此不會體現某一個國家的利益,從納稅人大會到工部局董事會及行政團隊,管理體制非常穩定、公開和公平,并且充滿了自治的氛圍。
香港的制度演進,則與上海則有所差別。當時的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直接發布《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規定香港的權力架構。人事上,總督是英王的全權代表,主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機關,并掌管香港的軍事。香港也只有一國“列強”,英國權力不受他國制約,香港的自治環境遠不如上海。
盡管如此,香港的制度演進仍有可取之處,英式殖民強調有效的管治,他們在意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這意味著要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賦予本地居民權力。同時,在政治和法律領域,英國也盡可能完整地將本土政治和法律體系移植到香港。
可以說,香港與上海的這次歷史性“同框”,深刻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發展方向。當中國的發展接入國際貿易的軌道,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城市的命運,隨即被改變了。
二、歷史變遷中的樞紐城市輪換
過去二百余年,中國貿易樞紐的稱號幾易其主,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上海取代廣州,二是香港取代上海,三是上海再次復興且與香港并駕齊驅。
1850s:上海取代廣州
廣州外貿之都一枝獨秀的地位,最近一次,確立于清朝乾隆年間(1757年)。當時清朝全面禁止對外貿易,僅保留了廣州作為對外通商港口,外商通過十三行等洋行、官辦商行與中國貿易,其它地區不允許通商。
此后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廣州一直壟斷著全國的外貿,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江海聯運的區位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從對外貿易來看,1830年前后,中國對歐美各國的海上貿易中,英國占到四分之三的份額,一直到鴉片戰爭后的很長時間段內,英國都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對象。從貿易金額來看,1844年,上海對英進出口貿易總值480萬元,廣州3340萬元;到1856年,上海對英進出口貿易總值3200萬元,廣州1730萬元,上海幾乎達到廣州的兩倍。
從關稅來看,1830年,江海關(上海)稅銀73,674.29兩,粵海關(廣州)稅銀1,663,635兩,到1875年,江海洋關稅銀高達3,608,000兩,粵海洋關稅銀1,709,578兩。
1850年前后,隨著粵海關關稅總額的斷崖式下跌,上海的關稅總額則一路上揚。對此,廣州并非沒有“反抗”過。當時,兩廣總督曾建言粵海關“用外國人治外國人,語言通曉,底蘊周知,內地奸民無從煽惑勾串,于稅務必有裨益”。然而,局面并未因此被改變。廣州當時因循守舊,且多有腐敗現象,外商無法在貿易中得到公平的對待。相較而言,上海則是冒險者的熱土,相對公平的氛圍給外貿行業帶來了更多喘息空間。
資料來源:[美]范岱克,2018: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這個時期,大批的冒險家到上海創業或開設分支機構,更多的是從廣州轉移過來的機構,像怡和(原渣甸)、寶順、廣隆、沙遜、旗昌等。隨著貿易北移,廣州開始衰落,人口向北方流動。上海開埠時,城區人口有27萬,而廣州高達70余萬,但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增至128萬,而廣州的人口反而少了20余萬。到1874年,中國超過70%的出口和50%的進口都要經過上海(Furuta,2000)。
超越廣州,遠遠不是上海最為高光的時刻,與廣州曾經擁有第一大港的時代不同,上海的崛起處身于中國與全球貿易迅速擴張的時代,這個時代產生的貿易總額遠遠高于廣州的高峰時刻。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上海的黃金時期。這時的上海不僅是全國的貿易中心,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文化和娛樂中心。金融方面,上海匯集了號稱“四行兩局一庫”的最重要的金融機構,是中國資金的調劑中心,也是遠東國際交易最活躍的金融中心,僅次于紐約和倫敦。商業上,有著名的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南京路四大公司,銷售全球最新上架的百貨。當時,最新式的科技和工程也大多由上海最早引進,再向全國推廣。
1949年以后:香港取代上海
建國之后,上海成為計劃經濟的支柱。在支持內地經濟建設的同時,上海出人出資源,支持小三線建設,上海的一些大學也遷至內地,這些都使得上海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有所減弱。
此后,承接上海留出空位的地方,就是香港。
其實,在開埠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并不起眼,那時的主角是上海,香港更多的角色是轉口航運中心。
這段時間,香港和上海的關系,可以從匯豐銀行的成立中窺得一斑。據《上海通史》陳述,由于中英貿易規模的上升,外國銀行開始趨向于本地化。匯豐銀行是第一家大型的本地銀行,其布局是以香港為總行,上海為主要業務地,匯豐香港和匯豐上海同時開業。上海盡管為分支行,但擬在上海成立董事會(后未有董事會,但規定持股與香港相同)。盡管香港是因割讓設立的殖民地,承擔一定的行政功能,但英國當時的發展重心是在上海。到1900年,香港人口不足30萬人。
建國后,香港的發展機遇主要有兩條:一是六七十年代趕上了東南亞經濟騰飛的快車,二是八十年代以后成為內地對外貿易的窗口城市。
二戰后,因種種原因,中國內地對外貿易停滯,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較大的打擊。1940年之后,人力資源優勢使得香港順利轉型為輕工業城市,生產紡織品、膠花、電子零件等產品。香港如今的富豪之中,有不少都起家于這些行業,如李嘉誠最開始就是做塑膠花的。香港也因此被稱之為“亞洲四小龍”。
1980年代以后,中國內地對外改革開放,制造業北移,香港的企業家開始向北進發。鄭少秋主演的《笑看風云》中,包家北上東莞開設紡織廠描述的就是這個背景。自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香港就是一直中國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占比保持在半數以上。這些資金有的是香港本地資本,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其它地區經由香港向內地投資。1990年以后,內地企業開始在香港證券市場上市,香港成為內地經濟主體資金融通的平臺。到今天,內地企業已經成為香港證券市場最重要的上市公司類型。
另一個直觀的層面就是貿易,盡管內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貿易權仍然沒有普遍向企業開放(一直要到中國入世以后),香港抓住機遇,重新調整為轉口貿易,再次成為內地對外貿易的窗口城市,中國各級政府創辦窗口企業專營進出口貿易,有中央層面的華潤、航空技術進出口,也有地方層面的豫港集團、津聯、粵海、越秀等。
這些因素都極大地拉動了香港經濟增速,也使得香港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直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僅次于紐約、倫敦。從經濟總量來看,改革開放之初,香港與上海的GDP與內地相比,都在8%左右。在隨后的十幾年內,香港經濟增速遠超內地,其GDP與內地的比重一度高至25%(1992年,以美元計價)。相反,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的開放力度不夠,滬港之間的差距被拉大。到1990年代,上海的GDP只有香港的20%。
香港回歸以后與中國大陸的合作后迅速發展,且呈加速態勢。貿易方面,據香港海關統計,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1997年約11161億港元,到2006年已經上升到23492億港元,增長超過一倍。目前,香港成為內地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地和第二大順著來源地。內地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地、進口和轉口對象。投資方面,自1986年始,到1996年,香港累計對內地直接投資項目約為16萬個,實際利用的投資金額為965億美元。到2006年底,香港累計對內地直接投資項目超過26個,實際利用香港資金達2770億美元;2005年底,內地在港設立非金融類企業2500多家,投資存量達365億美元,占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64%。2006年底,內地在港上市的企業達367家,市值67089億港元,占香港總市值的50%以上,成交總額的60%。
這一時期,在香港經濟一騎絕塵的背景下,曾經風光的上海未免顯得有些落寞。
2000s:上海復興、與香港并駕齊驅
改革開放以后,上海雖位列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但開放力度仍然不大。到1990年,其經濟活躍度已經落后于深圳。此時的上海,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低谷。1990年,鄧小平多次鼓勵上海改革開放,要像深圳一樣搞,次年他則明確提出“上海要開放”、“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開發浦東。隨后,上海開始浦東開發,推進各項改革。隨后,上海經濟開始騰飛,以高于香港近一倍的速度增長,并于2009年前后超過香港GDP。
2017年,上海口岸進出口貨物總值7.9萬億元人民幣,占全國的28.5%(《中國經濟報》),香港貨物進出口總值10,560億美元(香港政府統計處),兩者相差無幾。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設也頗具成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融資規模在最近十幾年的一些年份開始超越香港。
上海的復蘇,主要是中國經濟騰飛所致,9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口額占全球的比重從可有可無的角色躍居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大商品進口國。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球的12.8%(2018年數據,據WTO發布的《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美國排名第二,份額為8.5%。從這個角度看,上海復蘇的原因與150年以前上海的崛起毫無二致,作為中國經濟重心地區唯一一個可以江海聯運的中心城市,只要中國經濟可以融入全球,上海的經濟、貿易、金融等各個方面的體量在全球城市中必然會有一個顯著的地位。
隨著內地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香港作為服務貿易中心服務內地的角色,在亞洲金融風暴沖擊等因素的推動下,香港特區政府確立了“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經濟定位,并將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服務定為四大支柱產業,目前是建立香港自身的高增值服務體系,在支持內地的經濟發展、服務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重新確立自身的優勢地位。
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城市,多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四個中心,近年還明確了“科創中心”的角色),2009年,國務院批復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上海的這些舉措,毫無疑問是立足于上海是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連接點。很明顯,上海和香港的角色明顯有競爭的關系。
那么作為中國與世界的連接點,上海和香港誰可以勝出?表面上看,與上海身處中國內地的中心區位相比,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定位明顯差了一層,時間稍長,香港是無法和上海競爭的。長期致力于國際金融中心排名的Z/Yen公司每年提供兩次國際金融中心指數(GFCI)的排名,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長期保持了前四名,但新近的幾期排名中,香港下滑,第27期的排名中上海躍居全球第五,超過香港。
在這個時代的城市競爭中,區位依然重要,城市經濟腹地的規模也很重要,但這些都不再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特別是對于金融城市而言,制度和路徑依賴格外重要。2009年,復旦大學張軍教授提出一個看法:英語、美元和普通法系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他認為,金融中心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歷史結果。倫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后來紐約的崛起取代了倫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貿易中心。可是,銀行、資本市場等金融的發展,英國人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因為那些規則、合約、監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國形成的。倫敦再度成為與紐約一樣的國際金融中心,不是因為英鎊,而是因為美元在歐洲的擴張。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為倫敦再度成為金融中心提供了機遇。
正是因為它們有相同的基因條件,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動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當多的金融中心越來越依賴英語、美元和普通法系這三樣東西。從此,金融中心就有了一個模式,不容易發生變異,這即是金融中心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
按前述邏輯延伸討論,所謂的英語,指的是開放和全球化,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城市首先需要有足夠規模的國際商務旅行和外國人在此常住;美元更多代表了資金可以穩定和自由的流動,而普通法則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治理體系、習俗與規則不會輕易改變,商務與生活環境在確定性、適應性與連貫性可以很好的平衡。
不管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經驗,還是香港當下的現實,金融中心的發展,一是依賴于制度,這個制度可以和國際同類機構競爭,如稅收、金融監管、資金自由流動、法治水平,這些都是極為關鍵的要素,缺一不可。
在這樣的視角下來看,上海有大陸的腹地優勢,中國經濟體量如此之大,上海必然會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但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意味著上海要成為全球資金融通、交易的中心,那么就要問,全球其它地區的資金為什么要到上海這里繞個彎?與香港相比,上海目前還面臨一些制度性短板,短期內基本沒有替代香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地位的可能性。
三、樞紐城市:從區位到制度
水運的成本遠遠低于陸地。城市離不開水,長江、黃河以及京杭大運河,在物資輸送、戰爭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宋代以來的近世,海運和遠洋貿易漸起,海運堪稱近代以前的高速公路,運輸成本更低,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圍和地區維度展開貿易和文化交流。作為水運連接的節點,港口處于的城市,是貿易的集散地,帶來了金錢,也影響了制度。
Acemoglu等人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將西歐的崛起因而引起的東西方大分流的時間起點劃在1500年,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西歐部分國家通過大西洋與新大陸、非洲和亞洲有大量的貿易,這種貿易不僅直接通過彭慕蘭所說的通過海外殖民掠奪擺脫西歐本土的生態困境,還引發了體制變換,大西洋貿易的增長,提高了商人利益群體的議價能力,限制了君主政體的權力,保護了商人的財產權,這些制度上的進步對后來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
在交通成本決定物資輸送的時代,區位的地理優勢決定著城市的規模和地位,唐朝的兩京(長安、洛陽)及兩京走廊是達官貴人集居的地方,但東南部的經濟已經發展起來,物資向西北部輸運不便,城市發展的重心自然也會向東、向南遷。明清時代南方經濟向北京輸送的同時,也造就了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的繁榮,后來海運的興起及津浦鐵路的建設,讓運河沿線的城市衰落,鐵路沿線的城市興起,濟南、徐州、蚌埠等城市發展成為新的商業中心。在明清經濟重心南遷的背景下,長三角及長江流域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在內貿時代,上海并不是中心位置。但中國接入國際貿易后,上海就成為中國的中心,上海封閉以后,香港就替代了上海的位置。
回看過去150年滬港雙城樞紐地位的輪轉,在宏觀層面是由中國開放與否決定的:中國的兩輪封閉和窗口城市的需求造就了廣州和香港;中國的兩輪開放,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需求,兩次造就了上海。
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區位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地理的重要性決定了大城市出現的位置,因此培育出經濟規模和制度習俗。在交通成本日漸降低的時代,人和人之間的近距離依然重要,但人和人決定在哪個城市集聚則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路徑依賴很重要,制度也很重要。
上海和香港的輪換并不特殊,紐約也經歷了相近的過程。他以港口起家,最初主要向南方轉運小麥面粉,依托港口,紐約的制糖、紡織、服裝和出版業開始發展,隨著交通技術的發展,運輸成本開始大幅降低,港口的地位變的沒那么重要了。20世紀上半葉開始,紐約的失業率高、犯罪率也高。這時城市能不能擺脫衰退、實現復興,取決于他能不能讓聚集在這個城市里的人通過面對面的交流而創造價值。紐約成功的走出了衰退,重新發現了自身的價值,紐約的開放、包容,使得他可以持續的保持高密度人口及人口來源的多元,他們敢于冒險,勇于創新,通過金融、時尚等行業帶動了城市的復興(詳情可見格萊澤所著的《城市的勝利》)。
上海第一次崛起,有接入國際貿易時所處區位的優勢,也有廣州因循守舊、制度落后的原因。而深圳的崛起則復制了上海的道路,彼時的上海已經不再是改革的領頭羊,他恰如當年的廣州,而深圳恰如1840年之后的上海,沒有歷史包袱,銳意創新,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全國四個一線城市之一。
深圳的法寶說起來并不新奇,和當年的上海幾乎完全一樣,一是深圳有區位優勢,毗鄰香港,聯通內外,二是深圳作為特區,但歷史短,包袱少,比其它的三個特區更特,更加包容、開放,市場化程度更高,處于轉型中的國家,正式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如果嚴格執法,往往會挫傷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對于違法建筑、違規用人等現象也沒有下死手去打擊,也體現了深圳的包容。上海有“大”城市的先發優勢,香港也有國際化和普通法的優良傳統,但人并不必然會沿著這個路徑繼續集聚,他們還要看城市是否宜居,商業氛圍是否繁榮,當下這個時代,這個更多與制度相關。
因此,要檢視滬港兩地的未來,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只有厘清這兩個城市地位輪換的路徑,我們才有可能一窺它們的未來。
(感謝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汪天旸的相關數據收集和整理工作,感謝任冠青女士的建議和修訂。)
刊于FT中文網 | 2020-0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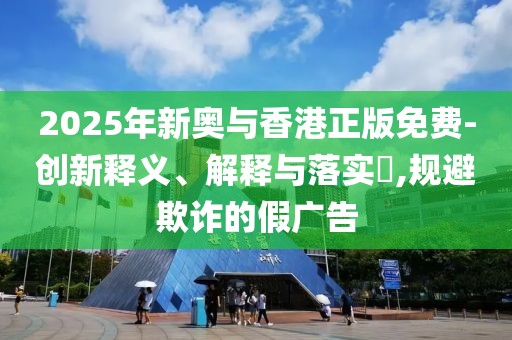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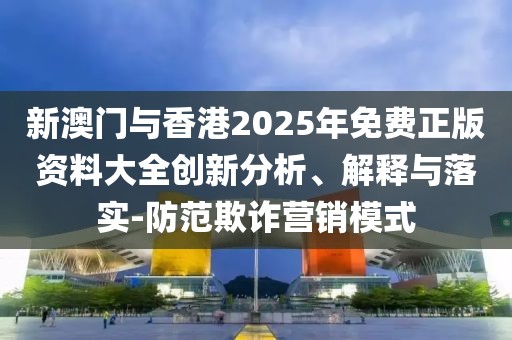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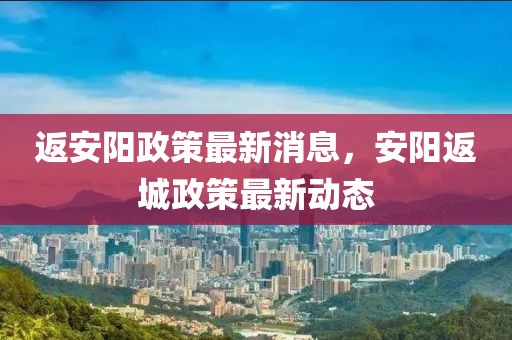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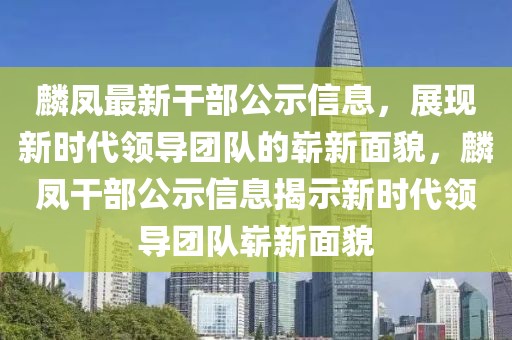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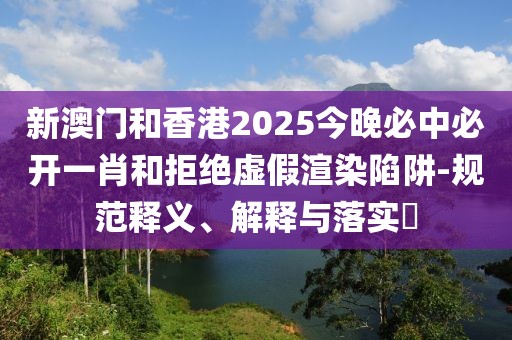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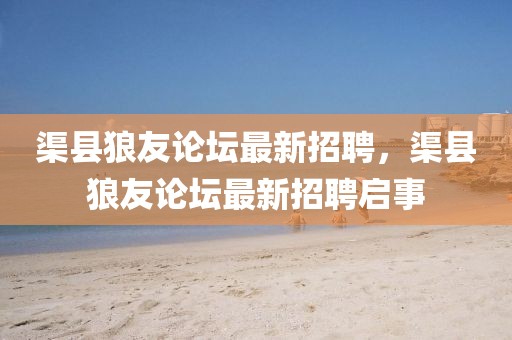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