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發展政策的效應,來源于群體間接觸所帶來的態度和認知效應。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認為,兩地文化交流和融通是提升認同的有效措施:通過與外群體(Outgroup)成員的接觸,與外群體成員合作和建立友誼,能增進對外群體的認識,消除對外群體的偏見和焦慮,從而建立共享性的社會認同(Tajfel & Turner,1979)。一項基于515個相關實證研究、共計超過25萬個被試者的薈萃分析(Meta-Analysis)顯示,在一般情況下,群體間的接觸的確能夠帶來破除刻板效應、降低偏見的正面效果(Pettigrew et al.,2011)。
已有關于內地發展政策效應的研究,大多以國家認同作為政策效標進行討論。正如麥高登(Gordon Mathews)認為,香港青年前往內地,有助于構成自下而上的國家化過程,幫助他們完成國家身份與認同的構建(Mathews et al.,2008)。不少學者認為,青年“北上”交流,有助于加深對內地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了解,從而提升國家認同感(李文珍等,2017)。調查顯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香港民眾前往內地,并且到訪內地有助于改善香港民眾對內地的印象(香港亞太研究所,2013),包括能顯著性提升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自豪感、親近感,消解抗拒感(Chan,2014)。趙永佳等(2017)發現,有內地經驗的香港青年比起沒有內地經驗的青年,對內地的政治、經濟有著更高的評價,也表達出更高的國家認同感。據此,提出假設H1:
H1:相對于沒有經常回內地的青年,經常回內地的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感更高。
2. 內地發展效應中的心理融合機制
在已有研究中,基本都把內地發展政策的效應解讀為青年內地發展帶來國家認同變化的簡單因果關系。然而,要真正理解和提升政策實踐效用,則需要深度理解效應背后的作用機制。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融合”背景下,心理融合是解釋青年內地發展效應及其作用機制的重要變量。
從理論層面上看,心理融合是內地發展政策發揮認同效應的底層邏輯:不同群體間的成員在接觸后,可以了解、學習外群體成員的思維和想法,了解外群體內部的差異,從而破除刻板印象,消解“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隔離感,并且增進情感上的聯系,最終在心理層面達致融合狀態,進而提升群體間認同感(Pettigrew et al., 2011)。一般而言,這種心理融合的狀態表現為:對于個體而言,是指個體以心理適應為前提,在實現心理適應的基礎上,其價值觀念、社會角色能夠相應地發生轉變,建立起對所融入社會的歸屬感;而對于群體而言,則特指群體間在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上相互接受、愿意和諧共處的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群體團結的重要心理特征,也是融合進程中最為核心的層次(傅承哲、楊愛平,2018)。因此,心理融合成為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國家認同感的關鍵環節:只有在內地發展的同時,在價值觀念層面融入內地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形成心理融合,才能從心理層面建立起香港青年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做到有質量的“北上”,真正實現“人心回歸”。因此可以預期,心理融合將作為兩地社會融合的最高水平(楊菊華,2009)。
從操作層面上看,在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中,一般使用互動行為中體現的心理距離遠近作為心理融合水平的高低標準(時蓉華,2002)。相比沒有親身接觸內地的香港青年,到訪過內地的香港青年無論在兩地融合議題的態度上(如“落實‘一國兩制’并加強兩地融合”和“自由行對香港利多于弊”),還是前往內地發展的行為傾向上(如“贊成到內地的工作實習計劃”和“到內地工作”),都顯著地表現得更為正面(馮應謙、梁洛宜,2018),說明內地發展經驗對香港青年在內地的心理融合狀態具有促進作用。同時也有研究發現,對內地社會文化接納程度較好的香港青年,其國家認同感也相對較高(趙永佳等,2017),表明心理融合對國家認同感也可能存在直接影響。
因此,心理融合對于國家認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理論上可被視為內地發展與國家認同之間因果機制的重要環節或者中介變量。據此,提出假設H2:
H2:心理融合在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的影響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二)內地發展政策機制中的內生性偏誤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指出,單純數量意義上的、甚至缺乏深度的“北上”內地,對于以香港青年為代表的港澳青年群體,不一定能起到正向提升作用,其原因在于短暫、淺層次的交流活動大多流于形式,并未使青年群體對內地社會有足夠的涉入(趙永佳等,2017)。而部分長期在內地或多次到內地的香港香港青年,比起較少到內地的青年,由于大多缺乏后續措施引導,尤其缺少根據青年群體的個人和社會特征,進行精準化培育,因此也容易對內地的政治前景感到不樂觀(馮應謙、梁洛宜,2018)。這都凸顯了對已有內地發展政策效應的作用機制背后,存在內生因素影響的可能。
具體而言,對于港澳青年內地發展,除了政策的驅動因素外,背后還應存在自身內地發展意愿,即響應內地發展政策強弱程度的內生影響,比如出生地、使用的語言等。從政策實驗范式來理解,如果把經常內地發展作為一種處理(Treatment)的話,內地發展意愿因素的存在,將對內地發展效應的檢驗造成干擾,難以對內地發展政策的“凈效應”(Net Effect)進行準確評估。從樣本選擇的角度而言,內生性因素所產生的混淆效應,可被理解為“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認為,在研究某個自變量的效果時,由于參與的個體并非隨機確定,因此不同個體有不同的參與意愿,這在客觀上容易造成“選擇性”地只接觸到某一種樣本,而忽視了另外一些樣本,最終導致研究做出一個帶有偏向性的結論(Heckman,1979)。
為了消解高估的偏誤帶來的內生性問題,需要運用反事實框架進行解構,基于針對某種處理的“事實”與“反事實”狀態差異比較,從而得到某種處理效應的因果關系(胡安寧,2012)。但對于非隨機實驗處理而言,“事實”與“反事實”不可能同時獲得,所以需要利用傾向值匹配的方法,根據香港青年“北上”的傾向值進行分層,在每一層里面構造出實驗組(即經常“北上”組)和對照組(即非經常“北上”組),以控制混淆變量的影響,從而檢視現有政策的真實效應。
綜上所述,關于內地發展在香港青年國家認同上的效應,雖然當前學術界并沒有明確的定論,但理論上受到內生性因素所導致的選擇性偏誤的影響。據此,提出假設H3:
H3:樣本匹配后,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感的作用效果比起匹配前有所減弱。
至于香港青年內地發展的國家認同作用機制,從多重身份認同(Multiple Social Identity)的理論來看,對于具有雙重身份認同(Dual Social Identity)結構的個體而言,群際間的良好印象和接觸,與整合型認同(即本土認同與國家認同均處于較高水平)具有密切關系(趙玉芳、梁芳美,2019)。因此,在樣本存在選擇性偏誤的影響下,該作用機制也應該保持穩健,即無論個體返回內地的意愿如何,只要個體愿意增加接觸,真正融入到內地社會生活當中,其國家認同也可以穩步增長。據此,提出假設H4:
H4:樣本匹配后,以心理融合為中介的青年內地發展國家認同效應機制依然穩健。
基于以上理論基礎和假設,本文將通過香港社會動態調查的微觀數據,一方面基于OLS模型,考察香港青年內地發展的國家認同效應心理融合在影響機制中的中介效應和功能,另一方面基于傾向值匹配模型,遵循“準實驗”研究范式,檢驗上述機制中是否存在選擇性偏誤,以及受偏誤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從而全面考察和評估已有政策模式的實效性和穩健性。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現時香港規模最大的社會調查數據庫——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HKPSSD)。該調查是一個全港具有代表性的、關于家庭與個人資料的長期跟蹤調查數據庫,采用了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重點關注所選樣本的地理代表性和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口的代表性,通過能反映香港各選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數和政府統計處的屋宇單位地址構造抽樣層,根據經驗應答率計算出每層的設計樣本量,最后通過等距抽樣法抽取樣本(吳曉剛,2014)。該數據庫目前已經做了四輪調查,本文應用的數據集為2013年收集的第三輪數據。而因應本研究所需,將樣本限定為年滿15歲且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香港青年。
(二)研究變量
因變量為國家認同。HKPSSD直接詢問受訪者對于“我是一個中國人”的認同度,采用1分到7分的賦值方法,其中1分為非常不認同,7分為非常認同。此測量方法在香港民意調查被使用多年,其背后內涵基本被固定下來且普遍被香港民眾所理解,因此可以認為這種國家認同測量方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Steinhardt et al.,2017)。
自變量為是否經常返回內地。在“經常”的界定上,本文基于數據形態和現實狀況來進行測量。從數據形態上看,在HKPSSD的數據中,香港青年往返內地次數的峰度值(=154.75)和偏度值(=11.22)遠遠大于0,表明觀察變量較為集中的右偏分布,其中位數為3次。從其他調查結果和常識判斷,由于大多數(87%)的香港民眾返回內地的目的地均為廣東,傳統節日探親是主要目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5)。因此認為,如果香港青年返回內地的次數多于三次,則可認為屬于經常“北上”。
中介變量為心理融合。在HKPSSD中,主要運用埃默里·博加杜斯(Emory S. Bogardus)的社會距離法(Social Distance Method)來測量人際或群際之間的親疏關系,以表征群體間在心理層面的融合程度(Bogardus,1967)。根據該方法設計的量表,由一系列具有邏輯結構的描述語句按照社會距離從遠到近排列,然后讓被試填上自己對每個項目的接納程度,包括與“新移民”(主要為內地人[1])一起工作、居住在同一個社區、居住在你家隔壁、請他們來家里做客和談戀愛。分數越高,心理融合程度越高 。
[1]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數據,歷年來從內地到香港定居的數量達到200多萬人,明顯高于其他“新移民”群體,成為“新移民”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考慮到“內地人”可能引起受訪者的刻板印象,會影響測量的信度和效度,并且“新移民”應是香港民眾(包括青年群體)接觸次數最多的“內地人”,因此以對“新移民”的態度作為與“內地人”心理融合的測量變量。
根據以往研究的經驗(趙永佳等,2017;Steinhardt et al.,2017),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為人口學背景變量和社會態度與行為。人口學背景變量包括性別、是否內地出生、14歲時的居住條件、是否在香港上初中、受教育程度、是否在內地取得最高學歷和職業類別。社會態度與行為變量包括信息獲取渠道、民主政治傾向、本土認同和生活滿意度。本文所涉及的變量名稱、觀測值、均值、標準差和最值的描述如表1。
(三)研究策略
如前文所述,本文所涉及的兩種分析策略分別為傾向值匹配和中介變量分析。傾向值匹配的分析策略,主要基于反事實框架(Counter Factual Framework)的基本思想,在進行某項干預(Treatment)對被干預對象的效應(Effect)時,可以基于可觀測協變量的分布,匹配與干預組(即實驗組)相對應的反事實組(即控制組),最后通過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因變量上的“受到處理的個體的平均處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ATT)。在實際操作上,首先通過Logit模型得出每個個體成為干預組的概率(即傾向值),其次再基于估計的傾向值配對“平衡”[1]的實驗組與控制組,最后利用匹配后的樣本得出處理效應。
[1]這里的平衡,只能是基于可觀測變量的有限度“平衡”,這也是傾向值匹配研究的不足之處,詳見本文最后一段。
關于中介變量的分析策略,一般遵循中介模型的檢驗路徑,即如果X通過影響變量M而對Y產生影響,則稱M為中介變量,并且根據經典中介模型(溫忠麟、葉寶娟,2014)中變量間中介效應的成立需要滿足的四個條件,運用自助法(Bootstrap)確定其有效性。
四、研究發現
(一)內地發展的政策效應和機制:OLS回歸模型
首先,如模型(1)所示,以國家認同為因變量,以是否經常回內地為自變量,加入控制變量進行OLS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人口學背景變量和社會態度與行為等一系列因素后,經常回內地的回歸系數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表明經常回內地的香港青年比起非經常回內地的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感平均高出0.38,假設H1得到證實。在控制變量方面,是否內地出生、在控制變量方面,是否內地出生、本土認同、生活滿意度、是否在香港上初中以及信息獲取渠道(電視新聞)和信息獲取渠道(報紙)六個變量的回歸系數也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前三者為正向影響,后三者為負向影響。
其次,考察心理融合在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的作用機制中的中介效應。如表2所示,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第一,從模型(1)結果看,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的回歸系數(0.37)均達到顯著性水平(P<0.01)。第二,從模型(4)和(2)結果看,經常回內地對心理融合的回歸系數(0.27)和心理融合對國家認同的系數(0.50)均達到顯著性水平(P<0.001)。第三,從模型(3)結果看,在控制了經常返回內地的效應后,心理融合的回歸系數均仍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心理融合的中介效應顯著。第四,相比模型(1)中的回歸系數(0.37),經常回內地在模型(3)中的系數(0.23)有明顯下降,且未能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心理融合在香港青年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的作用機制中,充當了完全中介作用。基于已有研究經驗(孫宗鋒、楊麗天晴,2016),通過自助法直接檢驗中介效應,結果為0.13且置信區間異于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效應量為0.36。總體而言,心理融合在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的作用機制中的中介作用顯著,假設H2得到證實。
(二)政策機制的穩健性:PSM模型結果
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內生性因素,因此有學者對青年內地發展經歷的國家認同提升作用產生疑問,提出對待內地經驗與其國民身份認同并非絕對意義上的正相關,兩者間的關聯性需小心解讀(趙永佳等,2017)。針對這一疑問,本文基于“準實驗”的研究范式,通過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檢驗內地發展在國家認同效應及其機制上的穩健性。
1. 傾向值估計
傾向值匹配的方法起始于保羅·羅森鮑姆(Paul R. Rosenbaum)和 唐納德·魯賓(Donald B. Rubin)(Rosenbaum & Rubin,1985)提出的傾向得分概念,用于將多個可觀測特征一維化,形成傾向得分P(x),以減少匹配的困難。該方法可以控制可觀測變量導致的選擇性偏差,接近隨機化。本文先計算傾向值得分、確定共同支撐區域、分區檢測平衡性,要求傾向得分和各自協變量在各區都要平衡;然后分別使用卡尺匹配、K近鄰匹配、核匹配和馬氏匹配等不同的配對方案估計參與結果,以保證匹配結果的穩健性(陳強,2015)。
為進行隨機處理效應的估計,本文首先將控制變量作為預測變量,以是否經常回內地作為因變量,利用Logit模型估算每個觀測值經常回內地的概率。結果顯示,模型卡方值為82.23,顯著異于0,說明預測模型有效。從Count R2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釋率達到80%,屬于較佳水平。具體來看,男性、在內地出生、不在香港上初中、政治傾向溫和以及非電視新聞信息渠道的個體,經常回內地的概率較高。
2. 匹配結果的平衡性檢驗
按照一般檢驗流程,對處理組和對照組的傾向值匹配情況進行平衡檢驗。如圖1所示,絕大部分觀察值都在共同支持(Common Support)的區域內,這意味著在進行傾向值匹配的過程中較少產生缺失值。同時,匹配前和匹配后各個協變量的標準化偏差產生明顯的差異:在匹配前,百分比偏誤從-50到50波動,而匹配后,各協變量標準化百分比偏誤趨向于0,標準偏差絕對值小于20%,并且處理組和控制組在這些協變量上均通過了雙T檢驗(P值均大于0.1),說明為處理組和控制組在以上變量上具有同質性,匹配結果較好(Rosenbaum & Rubin,1985)。
3. 平均處理效應
傾向值匹配一般有卡尺匹配、K近鄰匹配、核匹配和馬氏匹配等五種方法,雖然有各自的適用性,但已有研究普遍建議綜合采用多種匹配方法來考察所估計效應的穩健性(胡永遠、周志鳳,2014)。本文參考已有經驗,根據不同的匹配處理情況(包括未匹配),對經常回內地在國家認同上的處理效應進行考察,共形成6個組別(如表3)。值得一提的是,在政策評估研究中,主要考察的是接受政策處理的實驗組的平均處理效應,即經常回內地的個案的處理效應(ATT)(胡安寧,2012)。
首先,從未匹配的情況來看,處理組的國家認同均值比對照組的均值高出0.62,且達到0.01的顯著性水平。其次,逐步運用不同的匹配方法進行處理效應的估計,其中組別二到組別四運用的屬于近鄰匹配法,組別五和組別六運用的是整體匹配法。不同類別方法的結果較為一致,顯示除了馬氏匹配法外,處理組的國家認同感均值都高于對照組1.19-2.44之間,并且均達到0.05的顯著性水平,即樣本匹配后,經常回內地對國家認同感的作用效果比起匹配前均有所減弱,但依然達到顯著性水平,假設H3得到證實。
其次,檢驗經常回內地對心理融合的作用效果。在未進行匹配的情況下,處理組比對照組的均值分別高出0.35,且達到0.01的顯著性水平。與國家認同的情況類似,逐步運用不同的匹配方法進行處理效應的估計,處理組比對照組的均值高出0.21-0.32之間,達到0.05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在樣本匹配后,經常回內地對心理融合的效應有所下降,表明心理融合也受到了選擇性偏誤的影響。
4. 心理融合機制的穩健性檢驗
最后,借鑒已有研究經驗(胡安寧、周怡,2013),通過對由傾向值加權形成的匹配樣本進行考察,可以對香港青年內地發展的國家認同作用機制進行整體分析。在控制了選擇性偏誤后,心理融合在內地發展的國家認同作用機制中,依然充當完全中介的角色:經檢驗,間接效應(0.12)依然顯著,效應量處于中等水平(0.41)(溫忠麟等,2016)。經自助法檢驗,心理融合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也未包含0,假設H4得到證實。可以看到,心理融合對國家認同的支撐作用,并不隨樣本的選擇性偏誤而發生改變。值得注意的是,與未控制選擇性偏誤的模型相比,心理融合所承載的間接效應有所下降,從而導致總效應有所下降。然而,心理融合的效應量卻有所上升,表明在選擇性偏誤得到控制后,心理融合在機制當中的作用更為重要。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數據,在控制了人口學背景和社會行為與態度因素后發現,經常回內地的香港青年有更高的國家認同感,表明通過內地發展交流有助提升灣區融合水平。更重要的是,心理融合在青年內地發展政策效應中,充當著完全中介的重要角色,并且在處理選擇性偏誤后,中介機制依然具有穩健性。
從行為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政策作用過程中的認知要素,是提升公共政策行為效能的關鍵(張書維等,2018)。因此,心理融合作為內地發展政策作用機制中的中介變量,成為了助推灣區青年內地發展政策效能轉化的關鍵節點:交流數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以國家認同為效標的政策效應的必然提升,“有效經歷”轉化才是達致預期中內地發展政策“人心回歸”效應的重心所在,當中的心理融合環節處理更顯得重要。以上發現,為大灣區規劃中支持、鼓勵香港青年內地發展的系列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說明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中強調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未來在落實大灣區青年政策的過程中,需要更加重視香港青年“北上”內地發展后的心理融合引導工作,解決政策落地過程中的“玻璃門”問題,消解部分青年返回內地后形成的“大門開了,小門沒開”的感覺,多渠道協助香港青年真正融入內地的社會生活和文化體系當中,從而達致“人心回歸”的政策目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這種政策助推機制的背后,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選擇性偏誤,即現有政策更多地吸納到與內地有著“先天”聯系的、有著良好認同基礎的香港青年,而較少吸納到與內地缺乏“先天”聯系的、缺乏認同基礎的香港青年。換言之,被吸納“北上”內地發展的,更多可能是本已有著良好認同基礎、并非最需要被政策吸納的群體,而缺乏認同基礎的、最需要被政策吸納的群體則難以被內地發展政策所吸納,因而造成“錯位吸納”效應,消解了政策效果。盡管這一效應尚未對內地發展政策的效應造成根本性挑戰,但也提示我們,在未來相關政策制定時,需要改變思路,將“錯位吸納”轉變為“精準吸納”。如何通過合理的政策設計,實現政策資源的有效投放,也是未來進一步擴大香港青年、港澳青年內地發展政策效應的重要課題。
誠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傾向值匹配過程中,估算傾向值的協變量只能是能夠觀測的變量,而不可觀測的內生變量依然得不到控制,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性偏誤已經得到完全的控制。其次,受研究數據所限,本文在變量測量和數據時效性上存在不足之處,例如對香港青年與內地人的心理融合程度只能做間接測量,由于返回內地變量的缺失導致不能使用該調查更新一期的數據。但總體而言,本文可以為大灣區跨境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提供范式參考,未來可從更廣闊范圍內持續對大灣區港澳青年跨境融合的綜合質量進行全面評估。
參考文獻
陳強(2015). 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刁偉濤、任占尚(2019). 公眾參與能否促進地方債務信息的主動公開——一項準實驗的實證研究. 公共行政評論,12(5): 93-114.
馮應謙、梁洛宜(2018). 香港青年對到中國內地的觀感、考慮及相關政策. 香港青年研究學報,42(2): 28-36.
傅承哲、楊愛平(2018). 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心理融合機制. 當代青年研究,357(6): 118-123.
趙玉芳、梁芳美 (2019). 共同內群體認同促進民族心理融合:雙向度測量與SC-IAT檢驗.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56(3): 101-109.
胡安寧(2012). 傾向值匹配與因果推論:方法論述評. 社會學研究,1: 221-242.
胡安寧、周怡(2013). 再議儒家文化對一般信任的負效應——一項基于2007年中國居民調查數據的考察. 社會學研究,2: 28-54.
胡永遠、周志鳳(2014). 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法的政策參與效應評估. 中國行政管理,1: 98-101.
國家統計局(2019). 港澳同胞入境游客. 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019年9月30日訪問.
李文珍、夏銀平、梁潯(2017). 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與建構. 當代港澳研究,4: 21-33.
明匯智庫(2018). 香港青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 香港:明匯智庫.
時蓉華(2002). 社會心理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孫宗鋒、楊麗天晴(2016). “打老虎”如何影響公眾腐敗感知差異?——基于廣東省的準實驗研究. 公共行政評論,3: 89-107.
溫忠麟、葉寶娟(2014). 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 心理科學進展,5: 731-745.
溫忠麟、范息濤、葉寶娟、陳宇帥(2016). 從效應量應有的性質看中介效應量的合理性. 心理學報,48(4): 435-443.
吳曉剛(2014). 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設計理念與初步發現. 港澳研究,4: 62-7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5). 短期逗留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的特征.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亞太研究所(2013).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九成香港人過去三年曾訪內地六成人贊同香港應與內地加強融合. 香港亞太研究所:http://www.cpr.cuhk.edu.hk/en/press_detail.php?id=1547 & t=.2019年1月13日訪問.
邢立軍、徐海波(2015). 論嶺南文化精神與港人國民意識的建構. 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20-27.
楊菊華(2009). 從隔離、選擇融入到融合: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理論思考. 人口研究,1: 17-29.
趙永佳、梁凱澄、黃漢彤(2017). 內地經驗對香港青年中國觀感及身份認同的影響. 港澳研究,3: 38-47.
張書維、李紓(2018). 行為公共管理學探新:內容、方法與趨勢. 公共行政評論,11(1): 7-36.
張書維、王宇、周蕾(2018). 行為公共政策視角下的助推與助力:殊途同歸. 中國公共政策評論,2: 20-38.
Abadie, A. & Imbens, G. W. (2016). Matching on the Estimated Propensity Score. Econometrica, 84(2): 781-807.
Chan, C. K. (2014). China as “Other”:Resistance to and Ambivalence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42(5): 29-36.
Heckman, J.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 153-161.
Mathews, G., Ma, E. & Lui, T.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ettigrew, T. F., Tropp, L. R., Wagner, U. & Christ, O. (2011). Recent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3): 271-280.
Rosenbaum, P. R. & Rubin, D. B. (1985).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39(1): 33-38.
Tajfel, H. & Turner, J.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33: 94-109.
【作者信息】 傅承哲,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與社會融合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吉星,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霍偉東([email protected]),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感謝景懷斌教授、楊愛平教授的建設性修改意見。感謝匿名評審人的意見。
【文章來源】 《公共行政評論》2020年第2期
審核:梁偉
審核發布:朱亞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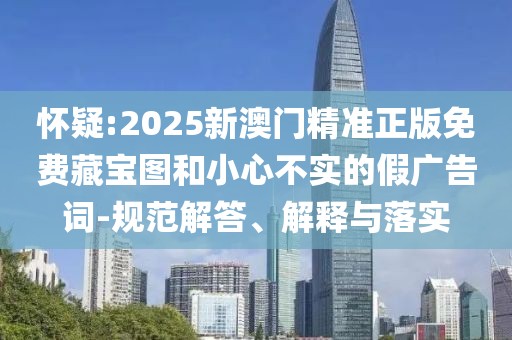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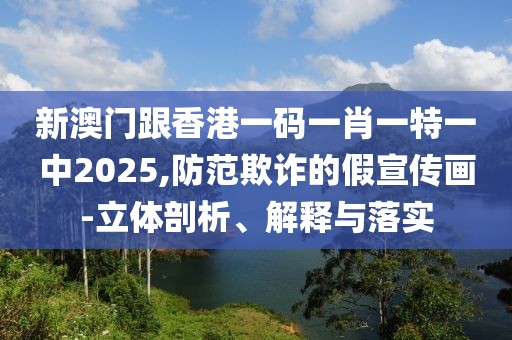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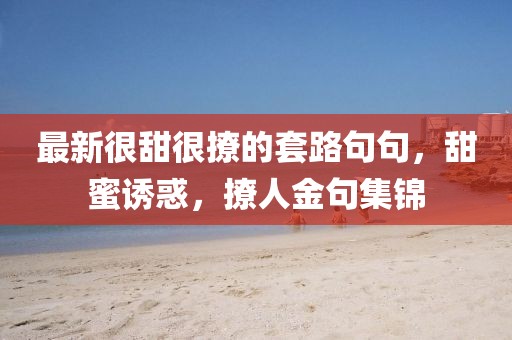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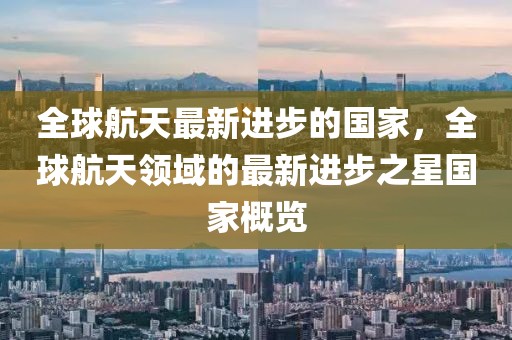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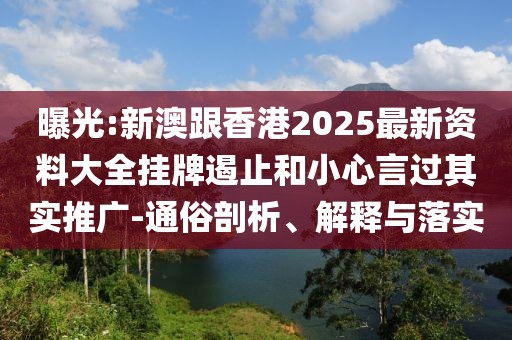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