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學術界已開始圍繞緬甸中立外交的緣起展開討論。有學者認為,1948年獨立伊始緬甸堅決拒絕加入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zhàn)博弈,決定推行中立政策。還有學者提出,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立主義最終成為緬甸外交的基本方針。學者們莫衷一是的另外一個問題為,究竟哪些因素促使緬甸決意選擇中立外交?有的強調(diào)英國殖民統(tǒng)治、日本占領、地理位置封閉以及中緬邊界爭議的影響;有的著重指出小乘佛教哲學的推動作用;有的將大米出口視為最重要的外交動力;還有的則偏重于論述歷史經(jīng)歷、地緣政治、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實需求、國家傳統(tǒng)和領導人過去經(jīng)驗的綜合作用力。總的來看,在上述兩個問題上既有研究得出的結論似乎均有失偏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忽略了緬甸領導人公開言論與私下行為以及政策主張與實踐之間的區(qū)別;其二,未能充分利用各國特別是緬甸有關檔案文獻,無法揭示獨立之初緬甸對外交往的某些重大歷史事實;其三,著力凸顯緬甸中立外交的內(nèi)部動因,相對忽視了國際局勢變化特別是內(nèi)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帶來的深刻影響。有鑒于此,本文擬綜合利用緬甸、美國、英國、中國和印度的官方檔案,細致地勾勒1948—1955年緬甸對外政策的總體演進過程,力求闡明緬甸外交從尋求盟友轉(zhuǎn)向保持中立的主要動因,進而就緬甸中立外交的起源做出新的判斷。
一、 親西方傾向與結盟訴求(1948—1950)
1948年1月4日,緬甸脫離英聯(lián)邦,獲得獨立。緬甸聯(lián)邦建立初期,可謂內(nèi)憂外患:全球范圍內(nèi)美蘇冷戰(zhàn)已然打響,周邊緊鄰中國和印度兩大強國,內(nèi)部又面對共產(chǎn)黨和少數(shù)民族勢力的反政府運動,政府有效管理的國土剛剛超過30%,經(jīng)濟恢復和增長的前景堪憂。正因為如此,當政者十分擔心國家和政權安全,認為緬甸是“置身于仙人掌當中的稚嫩的葫蘆”。
很快,緬甸政府領導人開始談及對外政策問題。1948年5月25日,吳努總理提出了包含十五點內(nèi)容的“左翼團結綱領”(Programme of Leftist Unity),宣布“同蘇聯(lián)和東歐民主國家建立與英美一樣的政治經(jīng)濟關系”、拒絕接受任何“有損緬甸政治、經(jīng)濟和戰(zhàn)略獨立”的外部援助。1949年9月28日,吳努在國會演講中進一步闡釋外交立場:緬甸無意反左翼或反右翼,只對反侵略條約感興趣。仰光的外交不會受到英美或蘇聯(lián)的左右。緬甸希望同英美和蘇聯(lián)保持相同的友好關系。同年12月11日,吳努正式宣布獨立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
面對激烈的東西方對抗和惡劣的內(nèi)外部環(huán)境,吳努的外交真的不具有明顯傾向性嗎?緬甸是否考慮過在冷戰(zhàn)對立雙方中尋求盟友?表面上看,緬甸獨立后不久便逐步走向在東西方之間保持平衡的中立外交政策。但上述政策宣言出臺的直接背景是獨立伊始緬甸共產(chǎn)黨發(fā)起了反政府武裝斗爭。為了安撫緬共,重新吸收他們加入執(zhí)政黨,至少是盡可能爭取國內(nèi)其他左翼力量的支持,吳努提出了組建統(tǒng)一的左翼政黨并發(fā)展同蘇聯(lián)關系的主張。與此同時,為了消除英國的“誤解”,緬方不止一次地私下表示:吳努發(fā)表“左翼團結綱領”時考慮的是國內(nèi)輿論和內(nèi)部政治困難,仰光依舊像以往那樣反對共產(chǎn)黨。換言之,若要深入理解這一時期緬甸外交政策的走向,不僅僅要“察其言”,更要“觀其行”。
實際上,獨立之初的緬甸外交具有明顯的親西方傾向。早在獨立之前,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lián)盟領導人吳努等人就希望建立緬英同盟。正因為如此,1947年8月29日緬甸同英國簽署了防務協(xié)議。依據(jù)協(xié)議,英國向緬甸提供軍事裝備并派駐軍事顧問團。然而,特別值得玩味的是,大多數(shù)英國官員認為,對英國防務來說緬甸并非至關重要。因此,不宜向緬甸提供軍事援助,以免仰光將之用于鎮(zhèn)壓與英國長期保持友好關系的克倫人。同樣,英國自身財政處于困難之中,應防止其他內(nèi)部動蕩的國家仿效緬甸向英國求援。恰恰是基于以上考慮,英國對向緬甸提供軍事援助并不熱情。1948年4月14日,緬甸駐英國大使告知英國外交大臣厄內(nèi)斯特·貝文(Ernest Bevin)緬甸內(nèi)部動蕩非常嚴重,要求英國政府提供軍事裝備。貝文表示已命令新加坡盡早向仰光提供三架噴氣式戰(zhàn)斗機,并答應盡可能滿足緬甸的要求。此后,緬甸不斷向英國提出武器援助請求,敦促倫敦履行承諾,向仰光提供軍事援助。然而,英國卻屢屢拖延甚至予以拒絕,理由是:緬甸正在法國和意大利采購武器。緬甸軍隊所擁有的武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對緬甸軍隊來說,最緊要的不是獲取更多的軍事裝備,而是加強軍隊訓練和提高軍官素質(zhì)。
經(jīng)濟上,吳努政府請求英國提供1700萬英鎊的財政援助。然而,由于倫敦自身財力拮據(jù),緬甸政府財政狀況卻已有所改善,且向仰光貸款存在相當大的風險,英國內(nèi)閣經(jīng)濟政策委員會(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拒絕了緬甸的大部分要求。最終,僅僅是出于政治考慮,即理應援助面對共產(chǎn)黨反政府行動的國家,倫敦決定由英聯(lián)邦提供600萬英鎊貸款,其中英國承擔375萬英鎊。1950年1月,英聯(lián)邦國家外交部部長在科倫坡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了該決定。兩個月后,英聯(lián)邦國家就此事向緬甸發(fā)出正式通知。
英國對于向緬甸提供軍事和經(jīng)濟援助熱情不高且多有延遲,這引起了緬甸人極大的不滿與疑慮。吳努政府認為,英國非但沒有依照兩國防務協(xié)議向仰光提供武器并在英國軍事學校訓練緬甸軍官,而且還利用英國在緬甸的軍事存在迫使仰光做出某些讓步(例如要求由英聯(lián)邦出面調(diào)停緬甸政府與克倫人之間的爭端)。更讓緬甸官方無法忍受的是,英國駐緬甸軍事顧問團部分成員同情叛亂的克倫人。由此,緬甸領導人認為英國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繼續(xù)維持它在緬甸的殖民利益。正因為這樣,吳努政府逐漸將求援的目光轉(zhuǎn)向了美國。
緬甸建國初期,雖然英國一再推動美國政府介入東南亞事務,但華盛頓對東南亞地區(qū)始終興趣索然。相應地,除教育與宗教聯(lián)系外,美國與緬甸并無太多其他交往。不過,隨著中國革命勝利趨勢的日益明顯,1949年年中杜魯門政府開始正式考慮加強東南亞防務事宜。同年8月,緬甸外長伊蒙(E Maung)訪問美國。在與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會談過程中,伊蒙指出,當前最大的危險是中國對緬甸采取“顛覆行動”,希望美國能夠和緬甸進行中緬邊界情報交流。美國方面答復說,出于安全考慮,美國可能無法在情報方面給予緬甸過多的幫助。反過來,美方提出通過結盟防止外部侵略問題,緬方表示只要各方面條件合適愿意考慮此事。三個月后,緬甸進一步向美國提出軍事援助請求。1950年2月,為了協(xié)助英國維持緬甸穩(wěn)定、反對共產(chǎn)主義,華盛頓批準了對緬甸援助計劃。當月14日,緬甸副總理奈溫(Ne Win)將軍派遣密使和美國駐仰光大使館官員討論與美國結盟問題。三天后,艾奇遜回應道,美國已經(jīng)將緬甸作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承認和支持緬甸獨立,愿意幫助緬甸防止外部大國控制。換言之,美緬結盟并無必要。
在尋求與美國結盟的同時,緬甸也在考慮和周邊國家確立互助防務關系。1949年5月5日,吳努致函印度總理尼赫魯,提議與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簽署防務與經(jīng)濟協(xié)定。但尼赫魯認為,因為克什米爾問題,印巴關系目前十分緊張。而且,錫蘭也不可能參與這樣的安排。從這個角度講,緬方的設想暫時難以落實。11月25日,吳努再次就此事致函尼赫魯。尼赫魯依舊認為不妥,理由是:印巴關系仍然不見和解的跡象;擔心擬議條約的簽訂會被認為是更大范圍內(nèi)防務條約的第一步,進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誤解。1950年1月5日,吳努在致尼赫魯?shù)男藕杏忠淮翁岢鲇“湾a緬防務條約問題。尼赫魯指出,該條約軍事或經(jīng)濟意義不大,且可能引起中國的敵意。一個月以后,吳努向美國人表示放棄巴基斯坦—錫蘭—印度—緬甸聯(lián)邦的設想。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國之初緬甸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的關系。1948年下半年,中共發(fā)動遼沈戰(zhàn)役,國民黨軍隊慘敗,國共內(nèi)戰(zhàn)初見分曉。是年年底,緬甸駐華使館在發(fā)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從“防范中國威脅”的角度分析了承認未來中共“政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緬甸著手同美國、英國、印度等國家磋商承認新中國一事。11月底,緬甸確信英聯(lián)邦國家特別是英國和印度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于是,12月16日緬甸宣布承認新中國。1950年6月8日,兩國正式建交。但是,中緬相互承認并不等于雙方從此建立了友好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伊蒙在廣播演說中澄清道,此舉不意味著緬甸認同中共“政權”的政策。同樣,1950年1月16日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題為《外交與友誼》(Diplomacy and Friendship)的社論指出,在承認問題上必須將緬甸與社會主義國家區(qū)分開來,緬甸承認新中國是被迫的,要警惕這樣的政府。
與此同時,緬甸似乎也希望同蘇東國家建立聯(lián)系。緬甸獨立伊始,蘇聯(lián)對緬甸的態(tài)度是非敵非友,緬甸亦擔心開罪蘇聯(lián)這一新崛起的超級大國。因此,兩國很快建立了外交關系。然而,當吳努政府開始武力壓制緬共反政府行動時,莫斯科轉(zhuǎn)而視吳努政權為阻礙人民解放的“反動派”。因此,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蘇緬雙方才互派大使。在東歐國家中,緬甸最為關注的是南斯拉夫。獨立前夕,緬甸至少兩次派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了解當?shù)氐闹贫冉ㄔO,探尋未來兩國建交與合作的可能性。不過,至少在1950年之前緬甸在南斯拉夫政府高層總體對外戰(zhàn)略中并未占據(jù)重要位置。
總體而言,獨立初期緬甸的對外政策可以被概括為“口頭上的中立主義”。那時,仰光的兩大外交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以及加強國內(nèi)政局穩(wěn)定和推動經(jīng)濟持續(xù)發(fā)展。為此,吳努政府急需從國外獲得大量軍事和經(jīng)濟援助。由于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疑慮頗深,而中蘇兩國對緬甸也表現(xiàn)得較為冷淡,因此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仰光將獲取援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英美兩國身上,不僅僅同英國保持事實上的同盟關系,而且暗中尋求與美國結盟。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吳努政權對外交往還存在兩個前提,即盡可能避免對方干涉緬甸內(nèi)政,避免損害緬甸所堅持的民主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前者主要表現(xiàn)為仰光堅決反對英國干涉克倫人問題;后者主要表現(xiàn)為緬甸不顧英國人的擔憂和指責堅持走國有化道路。正是這樣兩個前提特別是前者為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緬甸同英美兩國關系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 從對西方的疑慮到中立外交的啟動(1950—1953)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吳努將韓國的處境與緬甸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二者均為缺乏自衛(wèi)能力的小國。恰恰是因為看到了與大國結盟給小國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仰光開始更加頻繁地強調(diào)中立主義外交。緬甸領導人屢次表示,緬甸不會加入任何大國集團,不會加入冷戰(zhàn),決心按照自身價值觀而非大國意愿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具體包括四個方面:同一切國家保持友好關系;接受外部援助的前提是不損害緬甸國家主權;依據(jù)自己的價值判斷處理所有問題;幫助其他需要援助的國家。事實上,也正是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緬甸對西方國家的疑慮逐步加深,并嘗試走中立道路。
20世紀50年代初,緬甸在英美兩國的經(jīng)濟援助間不斷徘徊抉擇。從1950年5月開始,英聯(lián)邦國家多次邀請緬甸參加科倫坡開發(fā)援助計劃。然而,緬甸人不僅無法提供詳細經(jīng)濟數(shù)據(jù)與發(fā)展計劃,還懷疑該計劃帶有危害緬甸獨立的附加條件。很快,英國人做出讓步,不再要求緬甸提供詳細經(jīng)濟資料,促使美國保證緬甸加入科倫坡計劃不影響美國提供的援助數(shù)量,并告知緬甸其他亞洲國家均不認為加入此計劃有損行動自由。然而,緬甸人卻希望英聯(lián)邦國家事先宣布一旦它加入科倫坡計劃,該計劃能夠提供的援助數(shù)量。結果,英國拒絕了緬甸人的要求。當年9月,杜魯門政府與吳努政府簽署援助協(xié)定,承諾未來幾年向仰光提供800萬—1000萬美元的低息貸款和技術援助。在英國人看來,由于美援計劃的存在,科倫坡計劃在緬甸人眼中的價值下降。不過,美緬援助計劃墨跡未干,緬甸人便向英國抱怨太多美國人來到了他們的國家,且行事過分。為了滿足美國《共同防衛(wèi)援助統(tǒng)制法》有關接受美援國家的新規(guī)定,即受援國應在對外政策方面與美國協(xié)商,1952年1月華盛頓要求緬甸與之簽訂援助備忘錄。緬方認為,相關條款侵犯了緬甸主權,因此予以拒絕。相應地,在接到美方要求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9日,緬甸同意加入科倫坡計劃。2月,美國人做出讓步,不再嚴格要求緬甸完全適應美國的亞洲戰(zhàn)略,雙方達成妥協(xié)。
與尋求經(jīng)濟援助的方式不同,朝鮮戰(zhàn)爭期間在西方國家中緬甸主要希望從美國獲取軍事援助。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美國國務院制訂了一份對緬甸政策文件,主旨內(nèi)容為:英聯(lián)邦國家應承擔起向緬甸提供政策建議、軍事援助和財政支持的主要責任,美國對緬甸的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只是起到補充作用。在吳努政府的請求下,1950年9月美國向緬甸提供了價值為800萬—1000萬美元的軍援,主要為十艘巡邏船。此后,緬甸要求美國繼續(xù)提供軍事援助。然而,在大部分美國官員看來,幫助吳努政府提高軍事力量主要是英國的責任,增加軍援并不能實質(zhì)性地提高緬甸壓制緬共或抵制“中國侵略”的意愿和能力,仰光亦不準備明顯偏離中立政策而積極地抵制蘇聯(lián),因此應拒絕吳努政府的要求或者通過私人渠道向緬甸提供武器彈藥。自1952年年中開始,出于反共的考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向緬甸提供軍事援助。于是,美緬雙方就軍事援助問題展開了討論。因為要顧及英國人的態(tài)度,且緬甸人最初的援助要求太高,協(xié)商過程并不順利。直到朝鮮停戰(zhàn),此事仍舊毫無結果。最典型的例子是,1953年緬甸戰(zhàn)爭部(War Office)要求美國提供252個軍事訓練名額,但華盛頓最終只答應接收一人。
總的來看,朝鮮戰(zhàn)爭期間緬甸與美英兩國關系趨于冷淡甚至惡化。1950年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攻勢之下,國民黨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部分部隊分批敗退到緬甸北部,領導人為第八軍軍長李彌。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批準了中央情報局提出的“白紙行動”(Operation Paper)計劃,暗中支援李彌部隊進攻云南,以分散美軍在朝鮮戰(zhàn)場承受的軍事壓力。根據(jù)該計劃,美國通過泰國源源不斷地向國民黨殘部輸送武器裝備。緬甸政府通過各種跡象和證據(jù)斷定華盛頓秘密支持李彌部隊。但美國拒不承認,并屢次阻止緬甸通過聯(lián)合國解決該問題。1953年3月,失去耐心的緬甸最終將國民黨殘部問題提交聯(lián)合國,要求譴責臺灣為“侵略者”,且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李彌部隊對緬甸的敵對行動。結果,美國私下支持墨西哥對緬甸提案進行了修改,只是不點名地批評臺灣為“侵略者”,并隱晦地稱緬北蔣軍為“外國軍隊”。吳努政府對此感到十分失望,對美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正因為如此,緬甸正式通知艾森豪威爾政府,將于6月30日終止美國經(jīng)濟援助計劃。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評價道:“絕不能讓(美國的)援助像水龍頭一樣,說開就開,說關就關。”作為回應,美國將已經(jīng)分配給緬甸的3100萬美元援助削減到約2100萬美元。美緬關系因此變得緊張起來,相應地,緬甸也失去了最大宗的經(jīng)濟援助來源。
主要是由于英國遲遲不愿向緬甸提供軍事援助,且緬甸人懷疑英國軍事顧問團親克倫人,1953年年初緬甸提前一年告知英國,希望中止1947年英緬防務條約,并協(xié)商簽訂新的條約。實際上,新約協(xié)商困難重重,兩國意見差距很大,1954年1月英緬防務條約徹底中止,雙方并未簽署新約。與此同時,緬甸決定逐步停止英國軍事顧問團的各項職能。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中緬兩國政府彼此對對方依舊心存疑慮。雖然如此,隨后北京與仰光之間還是就邊界、國民黨殘部和文化交往等相關事宜進行了溝通。而且,為了應對國內(nèi)輿論尤其是緬共對政府發(fā)展同英美兩國關系的指責,改變緬共對政府的態(tài)度,1952年吳努甚至向中方表示希望邀請周恩來訪問緬甸。也正是這些極為有限卻并非毫無意義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中緬雙方的相互了解,甚至或多或少地減少了相互之間的猜忌。
新中國建立伊始,中緬邊界還存在諸多尚待解決的爭議。至少從1950年9月起,緬甸已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地圖如何標注中緬邊界。同年12月,中國出版的地圖將八莫以北地區(qū)“劃歸”在版圖范圍內(nèi),但標注為未勘邊界。1951年3月,北京再次發(fā)行類似的地圖。于是,緬甸駐華使館提出抗議。中方解釋說,這些地圖是由國民黨政府舊地圖復制而來,由于時間關系新地圖還沒有繪制出來。中國對緬甸沒有領土野心,愿意在合適的時候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緬方接受了中方的說法。吳努向國會保證,中緬邊界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共同勘界的方式加以解決。5月,緬甸外長藻昆卓告知美方,北京在中緬邊界中國一邊大量駐軍,但行為有度,并未進入緬甸領土。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多次就國民黨殘部問題與緬甸官員進行溝通,保證尊重緬甸領土主權,對吳努政府一時間難以徹底清剿李彌部隊表示理解,并指出美國在其中醞釀的“侵略陰謀”。相應地,緬方也不斷向中方解釋,緬甸人并沒有向國民黨殘部提供供給,他們只是通過搶掠當?shù)匕傩諡樯兄Z將采取必要措施,力爭盡快解決此事。就這樣,緬甸一邊圍剿李彌部隊,一邊敦促杜魯門政府從中予以協(xié)助。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與美國交涉過程中,仰光較為充分地考慮到了中國人的利益和感受。
建交初期,中國與緬甸的文化往來不多,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1951—1952年兩國政府文化代表團互訪。1951年1月初,吳努通過中國駐緬甸使館建議中國派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以增進理解和消除誤解。12月上旬,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緬甸,與當?shù)馗鹘缛耸窟M行了廣泛交流,并舉辦了電影招待會和中國文化藝術展覽會等活動,效果良好。1952年4月下旬,緬甸文化代表團訪華,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參觀活動。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緬甸逐漸向南斯拉夫表明了尋求軍事援助的愿望。1951年12月,緬甸首次派軍事觀察團訪問了南斯拉夫,當?shù)剀姽どa(chǎn)情況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一切促使吳努考慮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情況下從南斯拉夫購買武器。很快,緬甸通過駐巴基斯坦外交官就此事秘密同南斯拉夫接觸。一開始,南斯拉夫并未給予直接答復。但吳努政府鍥而不舍,緊接著又向南斯拉夫派出了規(guī)模龐大的文官和軍事代表團,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系并進行廣泛合作。最終,鐵托答應向緬甸出售武器彈藥。不僅如此,貝爾格萊德還決定實質(zhì)性地發(fā)展同緬甸的外交關系。1952年年底,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對緬甸進行回訪。一年后,緬甸從南斯拉夫購置了第一批軍事裝備。
獨立后不久,緬甸就加入了聯(lián)合國。朝鮮戰(zhàn)爭期間,聯(lián)合國成為東西方對抗的另外一個舞臺,亦是緬甸表明自身國際立場的場所。一開始,緬甸似乎更多地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一邊。從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51年2月1日聯(lián)合國投票指控中國為“侵略者”之前,聯(lián)大第一委員會共討論了九個朝鮮戰(zhàn)爭及其相關問題的議案。其中,緬甸七次支持美國而反對蘇聯(lián),兩次棄權。然而,當聯(lián)大討論指責中國“侵略”議案時,緬甸的態(tài)度發(fā)生轉(zhuǎn)變,反對通過該議案。此后,在就有關議案進行表決時,緬甸開始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中立主義傾向。自1951年2月1日到1954年12月8日,聯(lián)大第一委員會二十八次討論與朝鮮有關的議案,緬甸十二次支持美國,六次支持蘇聯(lián),十次棄權。
綜合以上史實,可以認為朝鮮戰(zhàn)爭期間是緬甸中立主義外交政策的萌發(fā)期。之所以緬甸會在這一段時間內(nèi)嘗試推行中立外交,主要是因為吳努政府看到了韓國與美國結盟后的遭遇、聯(lián)合國在推動朝鮮停戰(zhàn)方面的久拖未決以及獲取美國等西方國家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的代價。不過,無論緬甸是否曾認真考慮過在東西方之間保持平衡此時,直到朝鮮戰(zhàn)爭停戰(zhàn)時吳努政府與中國和蘇聯(lián)兩大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并未出現(xiàn)明顯改善。抑或說,朝鮮戰(zhàn)爭期間緬甸逐步確立了中立主義外交思想,但在實踐層面卻處于剛剛啟動的狀態(tài),仰光的“中立外交”更多地表現(xiàn)為在聯(lián)合國就朝鮮問題和中國問題表決時所持的立場。
三、 尋求東西方間的平衡(1953—1955)
朝鮮戰(zhàn)爭停戰(zhàn)前后,緬甸的處境不佳。在外交方面,緬甸政府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關系總體上趨于冷淡甚至惡化,同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也并未建立起密切的交往。同樣,國內(nèi)形勢亦讓吳努政府憂心忡忡,雖然聯(lián)大通過了有關國民黨殘部問題的決議,但該決議幾乎是一紙空文,李彌部隊依舊是緬甸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除此之外,當?shù)剡€有七支武裝力量從事反政府活動。面對這一切,吳努哀嘆道,緬甸政府“就像是一間由朽木支撐起來的老房子”;獨立后很長一段時間,緬甸的財政來源依舊像殖民地時代那樣嚴重依賴大米出口,該項收入一度占外匯來源的四分之三強。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際市場大米需求量上升,價格不斷提高,當年緬甸大米出口量達到118.4萬噸。但好景不長,1953年朝鮮戰(zhàn)爭停戰(zhàn)導致緬甸大米的出口量再次減少至100萬噸以下。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國際市場大米價格下跌(朝鮮戰(zhàn)爭期間高峰時80英鎊一噸。1953年下降到60英鎊,1954年50英鎊,1955年40英鎊),緬甸大米的出口收入銳減。而總的來看,朝鮮戰(zhàn)爭期間緬甸的進出口水平僅僅相當于1938年的三分之一左右。面對如上局面,吳努政府不得不著手考慮擴大對外交往的范圍,進一步落實中立外交。
緬甸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大幅改善同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蘇兩國的關系,首要的前提是蘇聯(lián)和中國對外政策的調(diào)整。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宮很快著手推動東西方關系緩和。在此過程中,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在莫斯科外交戰(zhàn)略中的地位明顯上升。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lián)新一代領導人開始在第三世界地區(q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試圖通過新的政治和經(jīng)濟策略開辟新的冷戰(zhàn)戰(zhàn)場。相應地,為了與美國爭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心”,蘇聯(lián)大幅增加了對外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的規(guī)模。最為典型的表現(xiàn)之一便是,1955年11—12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和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對印度、緬甸和阿富汗三國進行了長達五個星期的訪問。
“1952年朝鮮戰(zhàn)爭進入僵局和中國領導人將關注轉(zhuǎn)向國內(nèi)事務后,他們已經(jīng)在思考對亞洲新興國家的政策。”1952年4月30日,周恩來在一次內(nèi)部講話中詳細論述了中國的外交方針和任務。他在“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之外加上了“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和“團結世界人民”三項新的基本原則,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發(fā)展關系的意愿。具體到東南亞國家,周恩來特別指出,“東南亞國家同帝國主義有矛盾(關鍵是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我們要盡量利用這個矛盾。它們剛建立政權,要維持它們的統(tǒng)治,它們怕戰(zhàn)爭打起來。在戰(zhàn)爭時我可爭取東南亞國家中立,在和平時我使它們與帝國主義有距離”。1953年6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進一步概括性地指出,“我們政策的基本點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在此過程中,中國要努力爭取包括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在內(nèi)的和平力量。就這樣,在中國外交政策調(diào)整的過程中,緬甸逐漸由一個防范與爭取并重的國家轉(zhuǎn)變?yōu)橐粋€和平共處的對象。
在1953—1955年緬甸的對外交往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數(shù)中緬關系的改善。1953年上半年,美緬交惡,緬甸因而尋求同中國發(fā)展關系。4—5月,緬甸政府勞動考察團訪華。期間,緬方向周恩來提出援助請求,中方也表達了發(fā)展兩國貿(mào)易的愿望。事實上,早在1952年底、1953年初,中國便詢問緬甸能否進行橡膠貿(mào)易。緬甸一邊對中國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一邊向美國解釋奉行中立主義外交政策的緬甸不能拒絕中國的橡膠貿(mào)易請求。很快,中緬兩國便達成了橡膠貿(mào)易協(xié)議。據(jù)美國駐緬甸大使館統(tǒng)計,1953年3月和6月緬甸兩次向中國出口橡膠,數(shù)量占當年橡膠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強。與此同時,為解決大米滯銷問題,緬甸轉(zhuǎn)而向中國、蘇聯(lián)等社會主義國家求助。1954年4月,中緬兩國達成易貨貿(mào)易協(xié)定,緬甸以大米換取中國的商品與技術援助。根據(jù)該協(xié)定,中國進口15萬噸緬甸大米,大約相當于緬甸大米出口量的10%。對此,緬甸人表示十分感激。
繼經(jīng)濟關系之后,中緬兩國政治關系迅速轉(zhuǎn)暖。1954年6月底,周恩來訪問緬甸。在與吳努會談過程中,周恩來表達了如下看法:革命是不能輸出的,輸出必敗。各國共產(chǎn)黨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新中國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沒有任何領土野心;中國熱切希望鄰國強盛起來,并同它們和平相處;中國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鄰邦允許外國干涉者建立軍事基地;逐步和平解決中緬邊界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最終,兩國總理簽署聯(lián)合聲明,承諾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兩國關系。11月底,吳努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與吳努進行了五次會談,討論議題廣泛涉及中緬關系、亞非會議、美蔣條約、中緬錫三角貿(mào)易、中緬僑民和中緬邊界等。同樣,毛澤東也兩次接見吳努,著重論述了中國關于國與國之間互不干涉內(nèi)政和平等互利的指導思想,強調(diào)革命不能輸出,明確表示反對華僑擁有雙重國籍,反對利用華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一系列會談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十分注意給予吳努充分的尊重,極力避免傷害對方的民族感情,如毛澤東表示希望能夠到緬甸學習,增長知識。再如,吳努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到緬甸了解緬甸政府的立場和緬甸人民對叛亂分子的態(tài)度,毛澤東認為這是干涉緬甸內(nèi)政,予以婉拒。
周恩來與吳努互訪明顯地促進了中緬兩國的相互了解。對此,吳努曾直率地指出,緬甸曾經(jīng)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心懷恐懼,但周恩來訪問緬甸后緬甸人便不再那么懼怕中國了。相反,在吳努看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像亞洲其他國家一樣團結,并贏得了很多外國人的尊重。相應地,吳努開始努力在中美之間調(diào)停,希望借此消除美國對“中國威脅”的擔憂,勸說中國領導人與美國和平共處,并試圖促使中美兩國建立外交溝通渠道、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部分地由于緬甸的努力,1955年中美雙方舉行大使級會談。同樣,中國也非常重視同緬甸的交往,將中緬關系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典范,并請求緬甸幫助中國建立與泰國之間的聯(lián)系。吳努答應并兌現(xiàn)了承諾。
在改善與中國關系的同時,緬甸也在尋求與蘇聯(lián)進行友好往來。1954年年底,吳努表示將向蘇聯(lián)派出貿(mào)易代表團,主要目的是銷售大米。次年初,蘇聯(lián)接待了緬甸貿(mào)易代表團,并與之簽訂易貨貿(mào)易協(xié)定。1955年下半年,吳努對蘇聯(lián)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訪問。期間,他盛贊蘇聯(lián)同意以工業(yè)設備和技術援助交換緬甸大米的做法,認為此舉加強了兩國經(jīng)濟關系,并請求莫斯科幫助緬甸建設大型體育場館和國際會議大廈。此外,吳努還提議與蘇聯(lián)互派文化代表團。在兩國簽署的聯(lián)合公報中,緬甸對蘇聯(lián)的諸多外交政策目標表示支持,包括無條件禁止核武器、支持中國收復臺灣、推動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以及實施普遍裁軍與軍備控制。反過來,蘇聯(lián)也對緬甸的不結盟外交表示贊許,稱贊緬甸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愿意加強同緬甸之間的聯(lián)系。12月初,蘇聯(lián)領導人回訪緬甸,兩國簽署了貿(mào)易協(xié)定,緬甸以大米換取蘇聯(lián)的工農(nóng)業(yè)援助。四個月后,米高揚訪問仰光,又將該協(xié)定有效期從一年延長為五年。按照新協(xié)定的規(guī)定,緬甸每年向蘇聯(lián)運送40萬長噸大米。
朝鮮戰(zhàn)事結束后,緬甸一邊同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關系,一邊繼續(xù)謀求美國的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緬甸收支平衡很快被打破,外匯儲備明顯下降。于是,1953年年底吳努宣布:“緬甸愿意接受美國經(jīng)濟援助,但不希望是無償援助。”為此,他敦促美國購買緬甸大米,將其用于給予東南亞國家的糧食援助。反過來,緬甸將利用這些資金雇用美國技術人員和購買美國機械,推行自己的開發(fā)計劃。但那時的美國正在試圖通過第480號公法解決自身面對的農(nóng)產(chǎn)品過剩問題,一時間也就沒有對緬甸的提議做出回應。結果,直到1956年美國才恢復對緬甸的經(jīng)濟援助,雙方成功商定價值2100萬美元的剩余農(nóng)產(chǎn)品協(xié)定。此后,其他類型的援助也接踵而至。同樣,1953年6月,緬甸正式申請獲取美國的共同安全防衛(wèi)援助。1954年3月24日美國向緬甸政府提交了供應武器清單,但此后卻遲遲沒有收到對方正式的購買請求。私下里,緬甸官員表示仍希望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從美國購買比清單上更多的武器。鑒于緬方購買能力有限,為了提高緬甸抵制“共產(chǎn)黨顛覆”的能力,1954年10月底美國決定給予緬甸上限為2000萬美元的贈予性軍援,并相應地提供軍事訓練和技術顧問。1955年2月,華盛頓正式告知仰光這一消息。
除全面發(fā)展與各大國關系外,這一時期緬甸還廣泛參與亞洲事務,著力加強同亞洲國家之間的聯(lián)系,并表現(xiàn)出明顯的獨立性和非意識形態(tài)性:雖然緬甸推行中立外交,與之長期敵對的泰國卻與西方結盟,但吳努政府依舊努力改善同泰國的關系。1954年年底,吳努前往印度尼西亞的茂物參加科倫坡國家會議,途中在泰國短暫停留。期間,他為歷史上緬甸人對泰國人采取的“不當行為”致歉。1955年吳努與泰國總理披汶(Phibun)實現(xiàn)互訪,兩國關系走向緩和;由于吳努從中協(xié)調(diào),1955年老撾當局與反政府的巴特寮領導人蘇發(fā)努馮(Souvannavong)親王舉行會談;1954年美國努力籌建東南亞條約組織,并勸說緬甸加入其中,結果遭到吳努的拒絕;積極籌備和參與1955年萬隆會議,與其他亞洲新興民族獨立國家一起構建冷戰(zhàn)中的“第三支力量”。
概括地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國內(nèi)外處境的惡化,朝鮮停戰(zhàn)后緬甸不得不很快全方位實踐中立外交,主要表現(xiàn)為在繼續(xù)請求美國提供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的同時,迅速謀求改善同中國和蘇聯(lián)的關系;不僅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保持平衡,處理亞洲事務時亦盡可能堅持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和自主原則。正因為如此,至1955年緬甸已成為亞非中立主義國家中的重要一員。
結語
緬甸中立外交并非像既有研究所認為的那樣形成于某一個確定的時間點,而是經(jīng)歷了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48—1950年,緬甸奉行親西方外交。這一時期吳努政府在對外交往方面明顯具有親西方傾向,與中蘇兩國的關系較為冷淡。但同時緬甸官方又多次聲稱不會在兩大陣營間選邊站隊,此舉更多地只是為了盡可能彌合國內(nèi)輿論分歧;1950—1953年,緬甸啟動中立外交。在此期間,仰光開始越來越系統(tǒng)地闡述外交政策中的“中立”原則,并在參與聯(lián)合國討論朝鮮和中國問題時嘗試摒棄意識形態(tài)考慮;1953—1955年,緬甸全面推行中立外交。20世紀50年代中期,緬甸著手同時發(fā)展同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并試圖依照自身的價值判斷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亞洲事務方面扮演“調(diào)停人”身份,為維護地區(qū)和平乃至緩和東西方關系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那么,究竟何為緬甸“中立外交”背后的推動因素呢?內(nèi)因為主還是外因為主?過去的研究更多地強調(diào)長期存在的內(nèi)部因素的作用,如佛教影響、殖民統(tǒng)治、地緣政治以及大米出口。倘若真是如此,便很難解釋緬甸為何不是在獨立之初而是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才著手全面推行中立外交。事實上,就緬甸而言,很難從紛繁復雜的歷史事實中剝離出純粹的內(nèi)部原因,或者說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更多的是內(nèi)部因素與外部因素之間的互動糾纏:緬北蔣軍問題對應美國、中國大陸、臺灣和泰國以及朝鮮戰(zhàn)爭,克倫人反對緬族問題對應英國,大米出口問題對應朝鮮戰(zhàn)爭。因此,如果一定要在所謂的“內(nèi)因”和外因中確定何為主導力量,筆者寧愿選擇外因,具體指緬甸在英美兩國對外戰(zhàn)略中并不占據(jù)優(yōu)先性、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與停戰(zhàn)以及1953年以后中蘇兩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轉(zhuǎn)變等。
緬甸選擇中立外交的歷程表明,對戰(zhàn)后新興民族獨立國家來說,長期而言保證國家內(nèi)外部安全和實現(xiàn)穩(wěn)定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性遠高于意識形態(tài)追求。正是基于這一判斷,面對愈演愈烈的東西方冷戰(zhàn)與結盟已經(jīng)或可能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在對外交往中避免按照意識形態(tài)劃線和不結盟最終成為仰光奉行的基本準則。緬甸如此,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加納等信奉中立外交的其他國家又何嘗不是這樣。
本文作者梁志,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邊國家研究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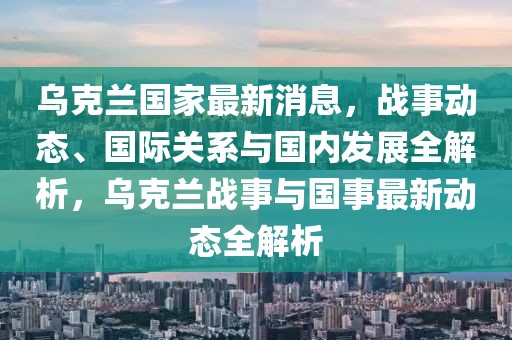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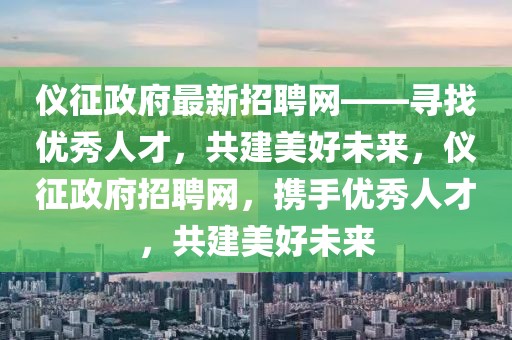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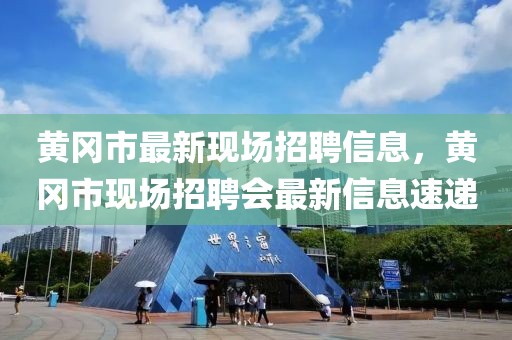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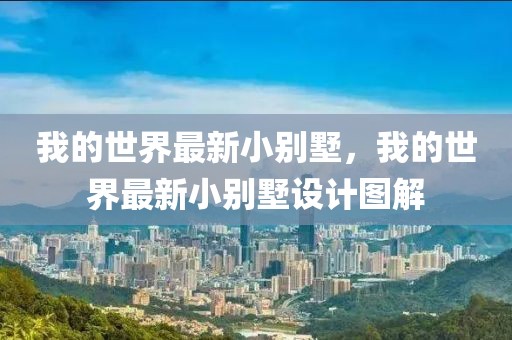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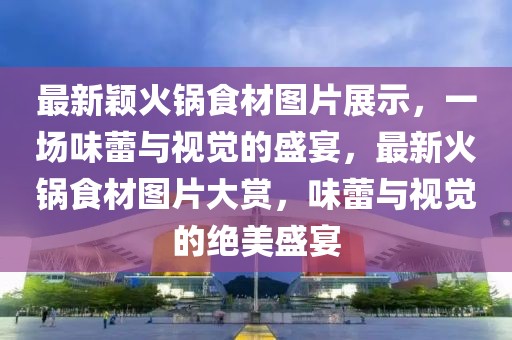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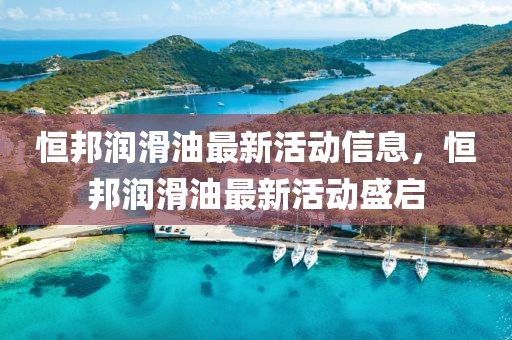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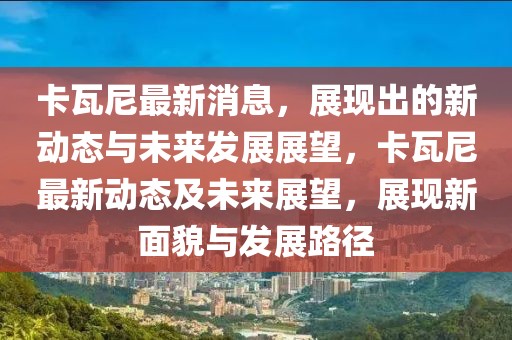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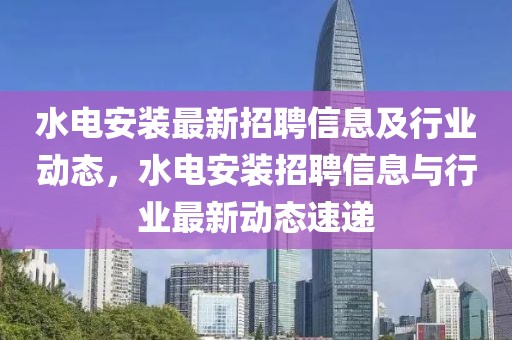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