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帶有宮崎駿半自傳的特征,而蒼鷺便對應鈴木敏夫。本片對莊生夢蝶、《愛麗絲漫游奇境》、黑澤明《夢》和今敏系列電影的要素,有所借鑒,恬靜淡然的世界都是表象,殘酷的世界真相卻是戰爭,能夠被觀察和解讀的,除了自身的心境之外,更多是這個世界給予的欺騙、壓迫和傷害。舅公是傳統的維新勢力代表,鸚鵡是法西斯的宣傳,學舌的它重復一千遍謊言,鸚鵡王則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本喻,代表著暴烈、殺戮、毀滅和因果。鵜鶘代表愚昧無知的群眾,它們總是被灌輸。惡的意識、死亡的意象無處不在,少年要想從惡托邦中飛翔出來,必須要親自摧毀,隕石代表日本明治維新,維新之后的日本民眾,既有了所謂的文明和科技,也有了戰爭因子和狂妄的征服世界的野心。
而少年和蒼鷺,要尋找新出路,要打倒十三塊積木構成的不穩定的自我投射,積木應該是權力的象征、以及軍國主義的思想鋼印。于是,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便取決于自己的選擇,怎么看待這個世界、走什么樣的路,便會有什么樣的人生。少年既是我,也帶有一定量的日本。正是無數的我構成了日本,這個國家有著復雜的過去。有左派和反戰,更有軍國主義和戰爭狂熱者。少年在異世界的行旅,是痛苦而迷惘的,美好和丑惡層層疊疊,進步和反動密不可分一體兩面,忘記過去還是銘記一切都似乎是不夠正確的。
本片就是一場夢境中的自由,如夢似幻的開放式舞臺,很有笛卡爾、《迷墻》和《黑客帝國》的味道。紅藥片還是藍藥片,就是林中不同方向的路。這很吉普力,沙漠上的風,熱乎乎、溫煦而孤獨。有我之境,對本片的解讀與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類似,人言言殊,各有所得吧。電影并沒有常規作品的第三幕結尾,即便宮崎駿傳達了他的反戰和環保的思想,但是他對“這個世界會好嗎?”依然是抱著猶疑的態度。當然,宮崎駿還是希望現在和未來的少年,能夠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這個世界終究是屬于少年的。
一百多年前,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某一次出門前,似乎自問自不答的說了句“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一輩子都在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最出名的事情是在1950年代和毛主席的沖突,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明白奧妙所在。每個時代的歷史問題是不同的,個體和集體都在歷史的縫隙中,在不同的“當代”觀察,都似乎是雙縫實驗,觀察就會對結果產生影響。觀察決定結果,執念扭曲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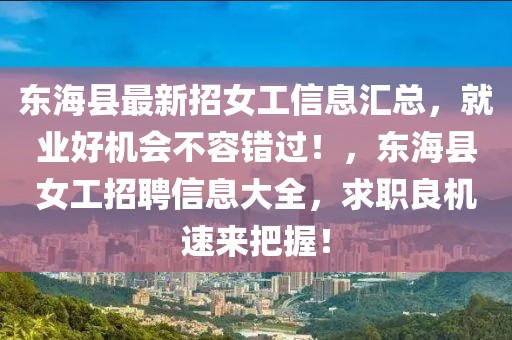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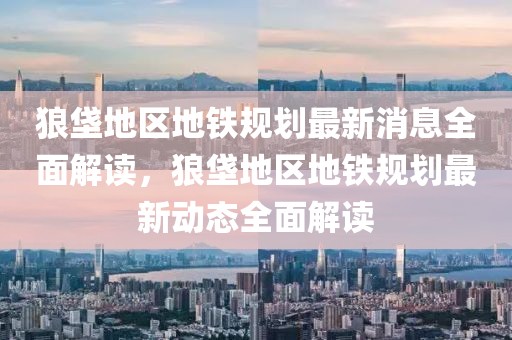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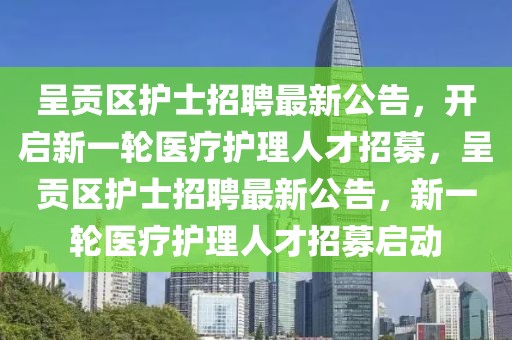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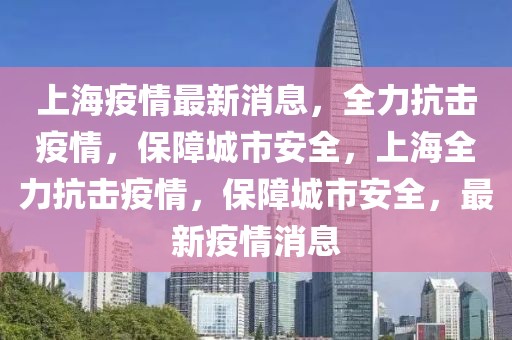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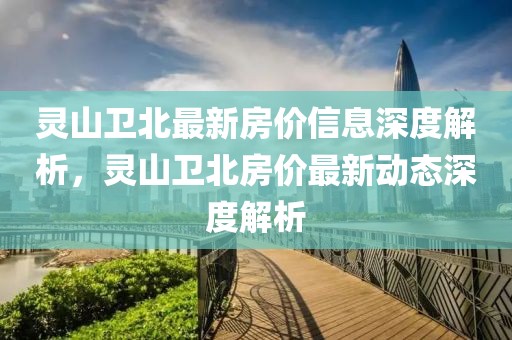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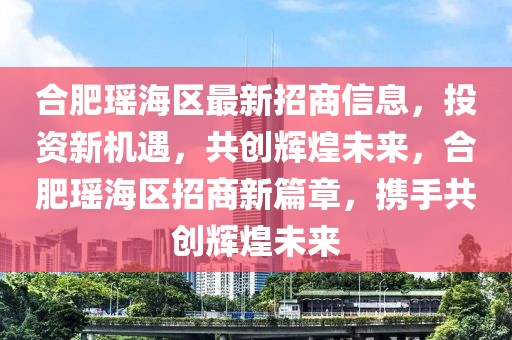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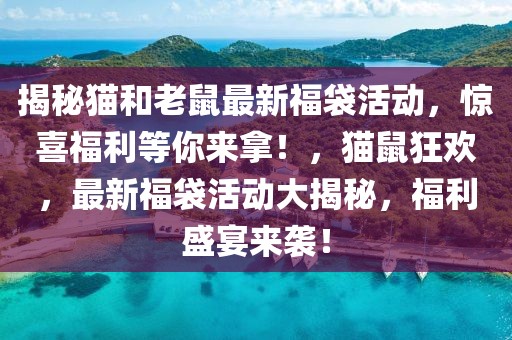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