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2022年11月25日)
“應盡我們所能改善美中關系,現在(做這件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美國史帶投資集團董事長、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現年97歲的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今年7月在《華爾街日報》的撰文中這樣呼吁道。
為發展更具建設性的美中關系,格林伯格還與十余名有中國經驗的美國商業和政策領袖成立了一個小組,并表達了與在中國有共同想法的人士開展坦誠交流、尋找解決方案的期待。
包括格林伯格在內長期致力于中美友好的人士提出的倡議,得到了中方的高度重視與積極響應。今年11月8日至16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王超率領一支高水平、多元化的代表團訪問美國紐約。據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官網顯示,代表團成員包括商務部前部長陳德銘,原國務院僑辦主任、原中央外辦常務副主任裘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前副主任寧吉喆,前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等。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作為中美關系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從1994年赴美做訪問學者,一直到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吳心伯奔走于中美,參與、組織學術交流,僅2019年,他就曾四度赴美訪問。正是在這二十余年無間斷的接觸中,吳心伯與美國的一些資深專家學者建立起深厚聯結。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期間,吳心伯分享了時隔三年再次訪美的見聞,以及對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經濟狀況、中期選舉的近距離觀察。
盡管熱烈、頻密的面對面交往正在恢復,美方各領域人士期待與中方加強交流的意愿強烈,吳心伯仍敏銳地察覺到美國社會對華氛圍發生著微妙變化:有的人說話變得謹慎了;在華盛頓“政治正確”風向的作用下,昔日對華“接觸”“對話”等表述被貼上了“壞詞”標簽;不同于熟悉的老一輩中國問題研究者,美政府和智庫里涌現出一批立場強硬的“新面孔”……
“隨著兩國關系所處大環境的變化,對美保持密切的接觸顯得更為緊迫。”吳心伯坦言其擔憂,在當前情況下,如何與美方開展有效、高質量交往與接觸,是未來年輕一代面臨的挑戰。
談及中美元首會晤后下一階段兩國關系的發展走向,吳心伯認為,美國中期選舉后,到2024年美國大選開始前的這一年,雖不乏干擾因素出現,兩國仍可能迎來一段關系改善的“窗口期”。
吳心伯在布魯金斯學會
高水平代表團訪美釋放積極信號
澎湃新聞:此次訪美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構成涵蓋多領域,包括外交、國防、經貿、學術、關鍵行業與企業等,這一安排有何用意?
吳心伯:在我看來,主要還是考慮到這次與美方對話的議題比較廣泛,覆蓋的領域比較多,涵蓋了政治、外交、國防、經貿、人文交流等。因此,代表團成員的構成也比較多元化。
同時,在與美方接觸的過程中,他們也對中方代表團成員多元化、高質量的對話水平非常贊賞。
澎湃新聞:注意到代表團訪美的時間點(11月8日至16日)比較特殊,時值黨的二十大閉幕后,又逢美國中期選舉。在此期間,11月14日,中美元首還進行了會晤。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有什么考慮?
吳心伯:這個時間應該是中美雙方商量后的結果。主要是考慮到我們黨的二十大和美方中期選舉的這兩大因素,正好也趕上了中美元首會晤。這樣一個安排是確保雙方的對話能夠反映各自國內政治的最新進展,同時,也讓雙方能在國內政治議程告一段落后,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考慮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問題。
如果是在中美國內各自重大政治議程之前開展訪問,有很多內容可能談不到也談不透,訪問效果或受影響。
澎湃新聞:外界有報道稱,美國史帶投資集團董事長、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現年97歲的莫里斯·格林伯格在推動中美代表團溝通的過程中發揮著“橋梁”的作用。在什么情況下,我們才能期待中美關系中有更多這樣的推動者出現?
吳心伯:在兩國官方關系困難的時候,需要更多非官方的民間人士,發揮橋梁的作用,扮演積極推動者。過去,在中美關系的發展中,我們也多次看到這樣的推動者。而在當前的情況下,還是要通過積極的交流,讓美方的一些關心中美關系發展的有識之士,愿意和我們一起來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這一點很重要。
其實,我們這次代表團訪美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美方也很重視,畢竟三年多沒有這樣(中方高水平代表團訪美)面對面的交流。所以,美方認為,這表明我們正在逐步打開國門,開始走出去。同時,這次是美方先提出的倡議,不僅得到了中方的積極響應,還派出這樣一個高規格、高水平的代表團,美方也很受鼓舞。
在我看來,在兩國關系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更要多開展此類二軌外交、民間外交。如此一來,才能夠推動更多美方的有識之士在雙邊關系中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澎湃新聞:外界有觀點認為,隨著中美關系氛圍的變化,二軌外交的效用已被削弱。同時,華盛頓決策的核心圈也不斷出現立場強硬的新面孔。在此情況下,年輕一代研究者怎樣才能與美方進行更有效的接觸?您有哪些建議?
吳心伯:過去,美國老一輩的學者、官員能以一種接納的心態同我們交往。這次訪美,雖然是近3年來第一次見面,但我們與美方大多數的交談仍比較坦率,這主要基于我們之間此前多年的交往和接觸。
但現在,美國社會對華氣氛發生了變化,美方對華研究隊伍更新換代也很快,有一些我們此前接觸不多的“新面孔”。同時,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看法也與以往不同,他們可能會有意識地回避,甚至排斥同中方人士的交往。
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加大對美接觸力度,以防人際上的連接變得淡薄,甚至脫節。坦白來說,今后兩國年輕一代(研究者)的接觸,比我們當年困難得多,這是他們面臨的挑戰。但加強接觸還有交往工作還是得去做。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對中國有獨到的認識。他曾說過,研究中國就是要“拉關系”,其實,我們和美國的交往也是一樣,今后怎么做,這是個挑戰。
吳心伯與兩位老一代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藍普頓(David Lampton)在一起(左側為李侃如,右側為藍普頓)。
華盛頓語境下的“接觸”與“對話”
澎湃新聞:回顧這趟美國之行,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吳心伯:到美國后,美方對我們的歡迎程度令我印象深刻。實際上,我們整個代表團從紐約入境時,走的是外交通道,這就是美方給予我們禮遇。在美期間,美方也很踴躍地幫忙聯系會晤人員。除了參加組織的會議外,還有不少美方人士親自到中方代表團駐地與我們會面。
我去華盛頓的時候,一些人也是直接到我所在的酒店來見面。遇到時間安排不上的情況,有人甚至一大早趕來和我吃早餐,邊吃邊聊。種種現象都表明美方同我們交流的愿望非常強烈。
此外,美方人士也期待隨著形勢的好轉,他們能夠早日訪華。他們多次提到,如果不來中國交流,他們就只能通過媒體上的一些不夠客觀的信息來了解和分析中國,這會產生嚴重誤判。
澎湃新聞:除了美方的熱情接待外,與疫情前您訪問美國的經歷相比,此次與美方人士的交流是否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吳心伯:和有些人談話的時候,我能感覺到他們比較謹慎。我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參加一場公開活動時,也專門點出了這一點,我當時說:有意思的是,美方現在把和中國的互動稱作“communication”(溝通)。而在過去,他們會把這種互動稱為加強接觸“engagement”或者對話“dialogue”。但現在,后兩個詞都變成了華盛頓的“壞詞”。
2018年時,現任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和現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曾寫過一篇文章(編注:“The China Reckoning”),聲稱美國對華接觸失敗了。所以,美方現在很少再提“接觸”這個詞。此外,在奧巴馬時期,中美對話處于高峰階段,兩國之間大概有上百個對話機制,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上臺之后,他們開始質疑這些機制的作用,認為其未能產生效果,只是“作秀”。所以,“對話”這個詞大家也很少提及了。
這其實也能反映出美國人很講“政治正確”,畢竟華盛頓是一個政治中心,大家都在揣摩政治風向。
澎湃新聞:此次美國中期選舉中,通脹問題成為美國民眾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對此您有哪些直觀的感受?
吳心伯:目前美國的通脹水平仍然較高,尤其體現在食品價格和油價上。一位美國的教授和我說,他養育三個孩子,每周都需要去超市采購,但現在有些食品的價格大概上漲了80%左右。這位教授還開玩笑說,如果不是自己有兩份工作,或許難以承擔現在的生活成本。
另外,大家普遍預期明年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同時美聯儲還在繼續加息。盡管不清楚經濟會衰退到何種程度,但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澎湃新聞:在中美關系的發展中,美國工商界始終扮演重要角色。不過,有輿論認為,美國工商界對華態度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在與工商界人士接觸的過程中,您的實際感受如何?
吳心伯:接觸下來,美國工商界人士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方面,他們期待看到我們更加靈活的疫情防控政策。在美期間,我們剛好看到國家衛健委11月11日宣布,對入境人員的“7+3”(7天集中隔離和3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5+3”(5天集中隔離和3天居家隔離)。美國工商界認為這是一個積極信號。
同時,他們也希望中方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擴大經貿合作,期待看到中國經濟在未來增強發展動力。
澎湃新聞:據您觀察,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下,美國工商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響?
吳心伯:在我看來,美國政府推動的產業鏈“脫鉤”、科技方面的打壓政策,讓美國的工商界感受到了一定的壓力。而且他們也認識到,美政府不大可能在上述領域放松政策。
不過,美國工商界內部也有一些建設性的聲音存在。但這些聲音和想法能在多大程度影響政府的政策,仍有待觀察。
中美“窗口期”有多長?
澎湃新聞:注意到在元首會晤之后,中美兩國的經濟、氣候、國防團隊近期都分別進行面對面溝通。您如何看待這些新進展?
吳心伯:在中美元首會晤以后,兩國關系的氣氛有所改善。據我在華盛頓的觀察,無論是官方、智庫或是媒體,他們都認為兩國領導人會晤的結果是積極的。
接下來,雙方肯定會加強交往和對話,包括恢復過去的一些對話機制,在一些具體的問題領域推進務實合作,這大概是近期中美關系發展的走向。
澎湃新聞:具體舉例來說,對于中美防長11月22日的會晤,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對于發展兩國兩軍關系的態度是真誠的,但基本前提是美方必須說到做到,信守承諾。”在您看來,“前提條件”意味著什么?
吳心伯:在我看來,中美之間對話機制的恢復,應該是跟兩國關系改善的步伐保持一致。前段時間,中美關系受到嚴重沖擊,兩國之間的一些對話機制取消或暫停。現在,要逐步采取一些改善兩國關系的具體行動,這樣才能為兩國恢復對話、推進合作創造條件。實際上,這是一個逐漸建立互信的過程。
澎湃新聞:據中美元首會晤后美方發布的新聞稿顯示,美國務卿布林肯將訪華,這次訪問有什么節點性意義?
吳心伯:布林肯擔任國務卿近兩年還未訪華,放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一般而言,美國新政府執政后的幾個月內,國務卿就會訪問中國。這樣看來,布林肯訪華的決定,本身也代表著美方希望加強和中方高層交往、對話的愿望。
此外,布林肯訪華期間,可能也將就明年一段時期內中美雙邊關系的發展與走向同中方進行磋商,雙方共同規劃。我在和美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一名官員見面時,也談到布林肯訪華的話題,美方表示正在為此做準備,包括接下來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可能也將訪問中國,這也是在為布林肯訪華打前站。
澎湃新聞:正是基于中美高層近期的一系列較為積極的互動,不少分析認為,中美關系迎來了“窗口期”。您對中美之間的“窗口期”有何理解?這個“窗口期”會有多長?
吳心伯:這個“窗口期”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的周期性對其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關系影響明顯。由于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表現不錯,拜登在處理對華關系上可以較少地受到國內政治的牽制。不過,到了2024年大選期間,基于國內政治利益的考慮,拜登政府或對中國表現得更為強硬。因此,從中期選舉之后,到2024年大選開始前的這一年,可以說是一個“窗口期”。
除了上述客觀條件外,能否進入“窗口期”還需要考慮主觀因素。在與習近平主席的會晤中,拜登也表現出了與加強中國合作的主觀意愿。中期選舉之后,適度改善對華關系,對實現拜登的外交政策目標也很重要。
不過,也有干擾因素存在。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控制了眾議院,其優先議題之一就是推動一些涉華議題,包括臺灣問題、新冠病毒溯源、經貿、人權等問題。這實際上也會限制拜登對華政策的推進。
2024年大選,誰是最終贏家?
澎湃新聞:您近距離地感受了今年美國的中期選舉。您認為這次選舉是否和以往有所不同?
吳心伯:整個美國都對這次中期選舉異常關注。很多人把這次中期選舉看作2024年大選的“前哨戰”。也有人把這次選舉當成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測試”。因為特朗普在這次中期選舉中支持的很多候選人否認2020年美國大選的結果,不少美國選民認為這挑戰了美國民主制度,紛紛出來投票,這也是此次選舉投票率比較高的重要原因。
從中期選舉的結果來看,共和黨沒有像預期那樣大勝,特朗普成為“最大輸家”,他提名的不少候選人也未能當選。結果出來后,我還問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一位教授,“是否又對美國的制度恢復信心?”他回復,“我感到有信心多了”。
澎湃新聞:您說到這次中期選舉是2024年大選的“前哨戰”,那么這次的選舉結果是否會對大選有所影響?
吳心伯:中期選舉之后,很多人都開始關心2024年大選了。特朗普在11月15日宣布要參加2024年的大選。在某種意義上,2024年大選已經提前開展了,這很有意思。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次中期選舉發出的信號比較明確,外界不太看好特朗普,這也可能迫使共和黨內部要考慮支持其他更有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所以,在我看來,雖然這次中期選舉的結果對共和黨來說不太理想,卻可能有助于該黨在2024年大選中的表現。
對于執政黨民主黨而言,盡管在中期選舉中的“小敗”(編注:保住參議院,僅失去眾議院)即是勝利,但這恐怕不利于該黨在2024年的選舉。受到這次選舉結果的鼓舞,拜登很可能會在2024年繼續參選。到那時,82歲的拜登如果面對的是共和黨新推出的一個50歲左右的候選人,他的形象和精神面貌顯然會遇到挑戰。
澎湃新聞:最近看到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州長德桑蒂斯很受歡迎,他是否具備潛力沖擊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吳心伯:在這次中期選舉中,德桑蒂斯贏得很漂亮(編注:以近20個百分點的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連任州長),呼聲比較高。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和特朗普將如何開展角逐“廝殺”。
除了黨內明顯的離心傾向外,特朗普目前還面臨一些麻煩事,不確定性較大。司法部11月18日任命了獨立檢察官對涉特朗普的兩個案件進行調查,包括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卸任后對政府機密文件的處理。
現在外界討論比較多的有5至6個潛在總統競選者,包括前副總統彭斯、前國務卿蓬佩奧等。目前看來,有意在2024年競選總統的共和黨候選人比較多,但是民主黨似乎還只看到拜登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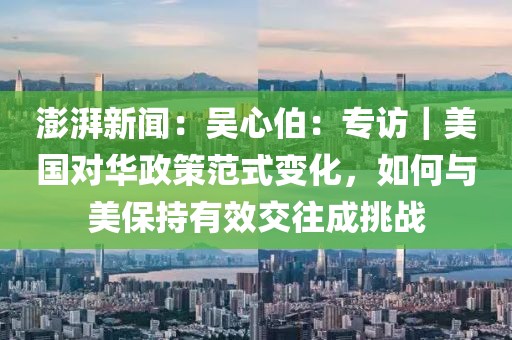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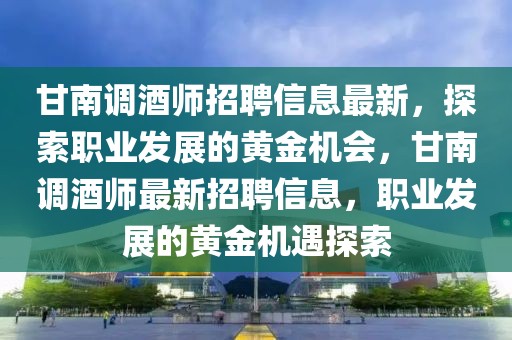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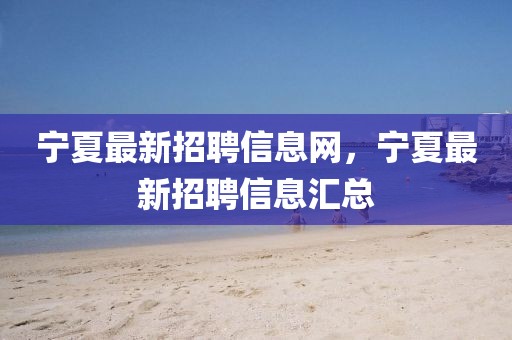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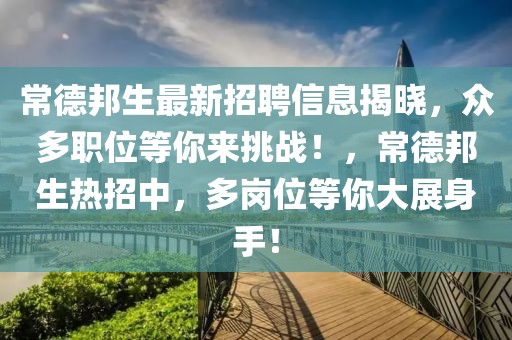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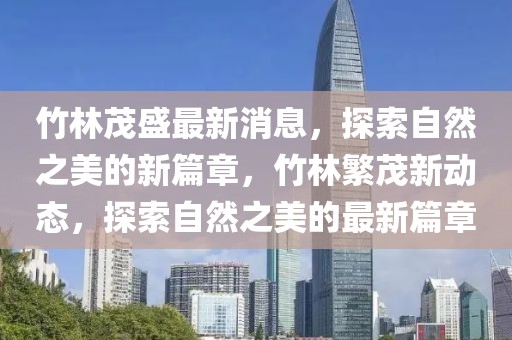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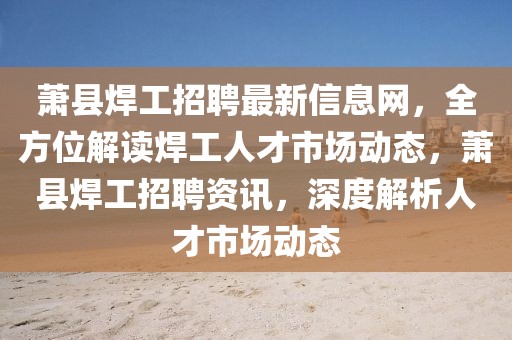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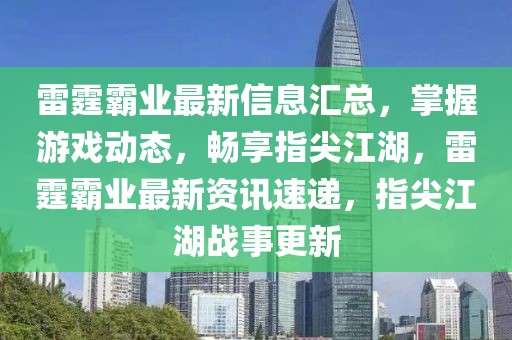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
魯ICP備2020050029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