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打著“陳思誠”痕跡的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一種共性:故作嚴(yán)肅的娛樂化。這種平衡的拿捏,在確保商業(yè)屬性之上的“嚴(yán)肅”包裝,其包裝方式達(dá)到的“模糊敏感點(diǎn)過審”與“形成宣發(fā)點(diǎn)”效果,當(dāng)然體現(xiàn)著主創(chuàng)對(duì)于商業(yè)電影的運(yùn)作能力,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成功,甚至是口碑票房雙收。但從客觀質(zhì)量而言,它終究難以觸及到真正的“優(yōu)秀”。陳思誠監(jiān)制的《誤殺3》,又是這種套路與結(jié)果的一次呈現(xiàn)。
《誤殺3》的核心在于“誤”字,它的最大誤會(huì)在于肖央對(duì)自己人生的誤解,他誤認(rèn)為自己的人生是無罪的,依然可以得到救贖,實(shí)際上卻已經(jīng)由于過去的罪孽而無從洗清。這構(gòu)成了他對(duì)女兒綁架案的態(tài)度,始終努力地讓自己認(rèn)為“一切都是外人的犯罪”,女兒的受困與自己無關(guān),而自己只是一個(gè)無辜受害的可憐父親,并沉浸在好父親的角色之中。
在影片的第一階段,肖央努力地尋找女兒,與綁匪周旋。此時(shí)的他與警察的關(guān)系非常簡單,警察將他當(dāng)成受害父親,而他則對(duì)抗綁匪。但是,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相應(yīng)的伏筆:警察調(diào)查著外人綁架女兒的監(jiān)控錄像,肖央也接到了綁匪的電話,二者看似是同盟,但肖央接完電話,說出“你們走吧,我自己解決”時(shí),他已經(jīng)留下了想要屏蔽警察、防止對(duì)方刺探自己真實(shí)過往、與綁匪關(guān)系的心理。而在序幕中,肖央看著女兒與佟麗婭公演的童話故事,故事逐漸變成了黑暗的童話,女兒被佟麗婭拋棄,隨后孤獨(dú)一人地說出“當(dāng)我們離開父母,就是長大的時(shí)候”,即是對(duì)一家人真實(shí)生活的映射,肖央看著一切,卻感動(dòng)地鼓掌,正是對(duì)自己真實(shí)生活的不自知:他身處在黑色童話與毀滅的紅色光線之中,卻還誤以為自己擁有的是美好的家庭,自己給女兒帶來了幸福的一切。這也是他在受洗儀式中的狀態(tài),即將完成泰國佛教里的受洗,卻在完成的瞬間反而遇到了女兒的被綁架,“黑暗真相”將他的罪孽生活揭露了出來,讓他的洗清無從實(shí)現(xiàn)。
在電影中,所有人都處在欲念之中,讓整個(gè)世界都變成了人間地獄。在開頭的部分,它就明確地給出了“全員皆惡”的概念。開車的嫌疑人是啞巴,在宗教概念中是“承受罪行”的存在,且在受審時(shí)嘲笑著警察,讓他的墮落更加明顯。肖央想要自己甩開警察,掩蓋著不堪的過去而解決問題,綁匪要引導(dǎo)他,并與他一起對(duì)付警察的跟隨,警察等于是在同時(shí)對(duì)付肖央的甩開與綁匪的陰謀。肖央需要聽從綁匪的命令去交贖金,警察則要對(duì)抗肖央的甩開,偷偷跟著肖央去查案立功,而綁匪則同時(shí)面對(duì)肖央與警察,以此構(gòu)成了三方的“互咬”連環(huán)套,絕對(duì)的正面存在就此消失了。
在肖央去交贖金的階段,三方的關(guān)系開始明顯地復(fù)雜化,肖央與警察轉(zhuǎn)向了潛在的對(duì)立,反而與綁匪有了一種同陣營感,這暗示了他的“有罪”,而警察也在不惜一切、無視肖央意愿地強(qiáng)行跟蹤,對(duì)應(yīng)著他們此前的毆打啞巴嫌疑人的“暴力之罪”。綁匪與肖央的對(duì)立則是基于“過往罪孽”的,肖央想要通過私自解決綁架問題來掩蓋自我,綁匪的目的則恰恰是借此完成對(duì)肖央的揭露。他讓肖央一個(gè)個(gè)回答問題,逐步承認(rèn)自己與貧民窟的童年過往,又將之直播在公眾平臺(tái),最后則是非常確切的”同化”:在肖央罪惡開啟的貧民窟中,命令肖央運(yùn)送另一個(gè)被綁架兒童,如佟麗婭此刻所說,“你這樣做,和他們有什么區(qū)別”。
并且,綁匪的要挾、肖央的順從,也形成了微觀層面的命運(yùn)不可抗,以此對(duì)接到了主題層面。肖央的目的在于救女兒、維護(hù)美好生活,但其過程卻是對(duì)過往罪惡的還原再現(xiàn),讓他的當(dāng)下生活重回過去狀態(tài),以示其“不可改變”,且作為公眾人物而被全社會(huì)所認(rèn)知,徹底改變他的名人當(dāng)下。肖央的動(dòng)機(jī)與結(jié)果的反差強(qiáng)化了這種命運(yùn)的必然性。
隨著肖央開始參與男孩的綁架,“重回當(dāng)年”,他的罪行也愈發(fā)明顯。肖央不得不運(yùn)送男孩,重走當(dāng)年參與綁架兒童的路。而在他的過往閃回中,對(duì)應(yīng)當(dāng)下肖央“主觀努力與客觀造成黑暗”的過往部分也出現(xiàn)了,綁匪打著“選孩子給富人領(lǐng)養(yǎng)”的美好旗號(hào),所行卻是偷渡孩子出海拐賣的犯罪,這是肖央眼中的過往,讓他作為孤兒偷渡者也參與了犯罪,只為了虛假的“脫離被拐賣命運(yùn)”,是“原點(diǎn)”對(duì)一切的造就與影響,又輻射到了當(dāng)下,讓他再一次為了救女兒而參與拐賣。
在肖央?yún)⑴c綁架男孩的階段,全員皆有罪的概念得到了具體化的表現(xiàn),又始終與他們的過往不堪相連接,從而呈現(xiàn)出了其罪孽的被迫性。作品給出了女綁匪的正面鏡頭,由此淡化其不可知的恐懼感,從“停留在變聲后的兇人”變成了明確的鮮活存在,在惡毒地威脅肖央之后,正面鏡頭中的憤怒表情首次扭轉(zhuǎn)了她的調(diào)性,與肖央過往的揭露同步,顯然是曾經(jīng)綁架案的受害者。這讓她隨后在照片特寫鏡頭中的“切手指”之罪,有了被迫的屬性,受困于綁架案造成創(chuàng)傷的過往,無從擺脫其對(duì)自己罪惡之心的引導(dǎo),與參與運(yùn)送兒童的肖央一致。肖央也同樣是如此,他在碼頭尋找自己的女兒,得到的卻是綁匪布置給自己的布娃娃,寫著“過去不可抹除”的大字,女兒給予的救贖是不可實(shí)現(xiàn)的,得到的只是“女兒”的沉淪死狀。
在這個(gè)階段中,作品開始用大尺度的血腥鏡頭與恐怖氛圍來表達(dá)主題。被砍下的女兒手指是女綁匪的罪孽,而肖央找到曾經(jīng)參與拐賣的女人的家,認(rèn)定她即是綁匪,是為了報(bào)復(fù)自己,對(duì)方同樣表情猙獰,雖然沒有拐孩子,卻借此向肖央要錢,雙方開始狂暴地互殺,也是他們的罪。在這個(gè)段落中,所有人都同時(shí)成為了兒童拐賣案相關(guān)的受害人,以及隨之被迫成為的罪犯。女兒綁架案視頻是“當(dāng)下的綁架”,即曾經(jīng)地獄到當(dāng)下的延續(xù),想要擺脫過往而不得之人也在其中互相殺戮,徹底暴露出罪惡的一面,一起被紅色的墻紙“地獄”所籠罩。
女綁匪主導(dǎo)了這一切,以此完成對(duì)綁架案的復(fù)仇。在這個(gè)段落中,女綁匪與肖央引出了過往的全貌:肖央運(yùn)送孩子們,發(fā)生了爆炸意外,女綁匪正是死亡孩子的母親。此時(shí),女綁匪成為了“過往”的唯一純粹受害者。但是,當(dāng)她來到當(dāng)下的時(shí)候,卻成為了最強(qiáng)大的有罪者,正是“全員被迫為惡”的最佳表現(xiàn)途徑。她同樣坐在了紅墻紙房間的“地獄”之中,而她的復(fù)仇對(duì)象也局限在了肖央等一線參與者的程度。
由此一來,作品就構(gòu)建了一個(gè)被迫有罪的人間地獄。女綁匪身處其中,與自己的同類進(jìn)行著互殺。但這只是綁架案與人間世界的低級(jí)別而已。警察局長達(dá)蒙才是更高層級(jí)世界里的真正掌控人,也是片中唯一的“主動(dòng)犯罪者”,不承擔(dān)任何創(chuàng)傷,而下界地獄中的一切,乃至于女綁匪,都是他的加害對(duì)象。拐賣船爆炸案是他的一手策劃,其中的所有人都陷在了深紅色的船艙之中,肖央想拜佛陀來“做完這最后一票”,卻在此時(shí)遇到了徹底將自己拖入地獄的達(dá)蒙策劃的爆炸。
這帶來了本片在罪孽與命運(yùn)等宗教層面之外的社會(huì)性內(nèi)容,即權(quán)力者釀成的人造地獄。這也是片中警察與媒體等“公眾社會(huì)引導(dǎo)來源”的作用。女綁匪曾經(jīng)求助于警察,卻沒有得到幫助。段奕宏等警察以正義之心追查案件,實(shí)際上卻是被沙蒙利用,作為抓獲肖央滅口的工具,讓他們同樣成為了一種“不自知的被動(dòng)罪惡者”。媒體也是如此,影片反復(fù)給到電視新聞的畫面,公眾想要得到真相,媒體也在討論著事件,最終卻是被達(dá)蒙利用:達(dá)蒙出現(xiàn)在鏡頭前面,宣示著自己的正義與肖央的邪惡。
女綁匪試圖對(duì)抗這一切,引導(dǎo)媒體,直播所有人的罪行,但她只能在第一階段完成目的。影片的第一階段是“底層被迫犯罪者的互殺”,女綁匪是其中的勝利者,將肖央的罪行直播到了媒體上。但當(dāng)影片來到第二階段,真正的主動(dòng)犯罪者達(dá)蒙出現(xiàn),女綁匪也就無能為力了,她試圖讓佟麗婭扮演的女老師“純潔符號(hào)”去揭露達(dá)蒙的罪惡,卻沒能將之播出到電視媒體中,自己落入達(dá)蒙之手。并且,這一階段的警察也超出了控制范圍,佟麗婭是“播出給媒體”的希望符號(hào),段奕宏則是警察正義的希望符號(hào),卻在此時(shí)被黑警反水殺死。
女綁匪曾經(jīng)寄托希望于段奕宏的妻子,此時(shí)則寄托于他,卻一樣地迎來了失敗,社會(huì)的希望不存同時(shí)存在于過往與當(dāng)下。肖央等人一起在船上對(duì)抗達(dá)蒙,綁架與炸彈都是對(duì)當(dāng)年案件的再現(xiàn),意味著往日命運(yùn)的不可脫離。拐賣兒童帶來了強(qiáng)烈的表達(dá)效果,上層者玷污了最純潔的存在,由此奠定了其對(duì)最深度黑暗的無法洗清。肖央在沙蒙的強(qiáng)迫之下,為了救女兒只能按下起爆器,正是對(duì)過往命運(yùn)的最終皈依,其掙脫的努力也是對(duì)皈依結(jié)果的引導(dǎo)而已。
在影片的結(jié)尾處,我們明顯看到了導(dǎo)演在尺度上的勉力。作為大陸上映的電影,它必須淡化宗教意味“迷信”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批判性,不能將一切落到宗教宿命論與徹底的批判之無望。
本片的落點(diǎn)正是二者的結(jié)合。因此,導(dǎo)演給出了一個(gè)盡量拿捏的結(jié)局。它先帶來了社會(huì)的有希望。女綁匪戰(zhàn)勝了達(dá)蒙,將一切播到了電視媒體上。而”警察”也是如此,段奕宏與女綁匪合作,身藏的攝像頭拍下了沙蒙的一切。這淡化了段奕宏等人以死亡和失敗對(duì)應(yīng)的“臣服于上層者給予之命運(yùn)”感。更大的處理則是佟麗婭的處理。她先是以黑色裝扮的姿態(tài)“復(fù)活”出現(xiàn),帶來了其作為“純潔希望符號(hào)”的打破,同樣深陷在了罪惡的參與之中,且同樣是達(dá)蒙爆炸案的受害者,在當(dāng)下依然無法獲得新的生活,而是要參與到殺人與綁架之中。隨后,她又揭示了一切的真相,帶來了反向的極致“光明”,甚至由其“反轉(zhuǎn)”而推翻了影片在當(dāng)下的核心“犯罪事件”,即肖央女兒綁架案,它從開頭即是佟麗婭與段奕宏等人的設(shè)計(jì),是女兒一起參與的表演。在對(duì)此前一切“大尺度與恐怖氛圍”內(nèi)容的真容再現(xiàn)之中,尺度與恐怖被淡化,其案件的罪惡性也不復(fù)存在,成為了絕對(duì)的正義執(zhí)行。
這帶來了影片結(jié)尾處的強(qiáng)烈情感化氛圍,佟麗婭等人回憶著他們與子女的親情,大段的閃回柔化了他們的形象,對(duì)沖了他們深度犯罪的黑暗,也讓段奕宏與佟麗婭等受害人也從中徹底變成了“無罪者”,隨后則是肖央的歸案,以此確立影片在價(jià)值觀調(diào)性上的“正確”。但這也恰恰是影片的問題。雖然已經(jīng)采取了“東南亞某國作奸犯科”的規(guī)避審查打法,但大陸電影終究要在表達(dá)尺度上受到限制。本片的當(dāng)下內(nèi)容實(shí)際上是對(duì)過往案件的再現(xiàn),以二者的對(duì)比去表現(xiàn)人物之于過往罪惡的不可脫離,而一切罪惡又來自于上層者在過往對(duì)童真“純潔”的玷污,并在當(dāng)下繼續(xù)打壓,上層者才是真正的現(xiàn)實(shí)維度中的“命運(yùn)宣判者”,是超出佛教之神的有力存在,以此引出了現(xiàn)實(shí)層面的主題,也完成了類型化的懸疑探案架構(gòu)。
因此,過往部分是重中之重。它先是被掩蓋著,呈現(xiàn)為表面的美好當(dāng)下,隨著女綁匪的行動(dòng)而逐步揭露出來,兩方對(duì)比之下,當(dāng)下的“掙脫成功”被愈發(fā)打破,過往的事件細(xì)節(jié)與人物罪惡暴露,當(dāng)下也成為了等同于它的狀態(tài),帶來“上層之神決定永恒命運(yùn)”的主題內(nèi)容。但這樣一來,影片就要大量涉及到官員的墮落,為了表現(xiàn)細(xì)節(jié)、豐滿案件合理性,更是要加入大量而具體的各機(jī)構(gòu)運(yùn)作模式,如何買通各環(huán)節(jié),而犯罪相關(guān)的正面描寫也必然更直接且大尺度。更重要的是,為了強(qiáng)化批判性,它理應(yīng)將所有人都變成徹底的罪惡者,并給予上層者以徹底的勝利。對(duì)于一部院線片來說,這顯然是超綱的。
因此,它只能盡量淡化過往事件的細(xì)節(jié)。成片中牽涉進(jìn)了很多人物與立場(chǎng),肖央為首的各一線人員、達(dá)蒙的上層者,肖央童年、拐賣兒童的兩個(gè)時(shí)間維度,卻無一例外地“大而化之”,全部匆匆一筆帶過。特別是針對(duì)碼頭爆炸案的過往部分,隨著他們的逐一出場(chǎng),在女綁匪的引導(dǎo)下與肖央互動(dòng),這個(gè)讓所有人深陷罪惡最極致深淵的最核心事件本應(yīng)該逐漸豐滿起來,像拼圖一樣地經(jīng)過各人的記憶而變得完整,由此帶來劇情的揭秘、人物的真容,再對(duì)比出當(dāng)下的“表面改變,實(shí)則不變”,讓人物在被引導(dǎo)中逐一接觸相關(guān)人,愈發(fā)面對(duì)曾經(jīng)地獄中的記憶,在當(dāng)下的狀態(tài)也漸漸地回到了彼時(shí)的自我之中。
作品想要展現(xiàn)的是,一線人員們參與曾經(jīng)的犯罪,讓他們?cè)诋?dāng)下同樣無法脫離這種心境,連配角女司機(jī)沒有參與綁架,都想勒索肖央,圖一筆財(cái)。但是,他們的狀態(tài)更多由最表層的“暴力尺度”呈現(xiàn),大喊大叫、互相廝殺,以及幾個(gè)血腥特寫,而真正重要、同時(shí)關(guān)于人物塑造“罪惡不可解”與劇情內(nèi)容(過去發(fā)生了什么)的過往事件細(xì)節(jié),卻都停留在了單薄生硬的“空口說臺(tái)詞”上。這部分內(nèi)容先由他們自己與女綁匪敘述,到了結(jié)尾才有了肖央與沙蒙的幾次回溯給出正面段落,卻也非常有限,不過是對(duì)最高潮部分的“碼頭爆炸”的反復(fù)回放而已,其尺度之遮掩,甚至吝嗇于給到死亡兒童的正面鏡頭,只有寥寥幾個(gè)遠(yuǎn)景。至于過往案件中的更多部分,就更是無從談起了。達(dá)蒙參與的綁架案具體運(yùn)作,兒童們?cè)凇氨槐锼?炸死”之外還遭遇了什么折磨,以及更外延的肖央童年,都是完全缺失的。
此外,它還能加入肖央在碼頭岸之后的過往部分。他成為了富商,其致富過程中顯然存在著與沙蒙或其他上層者的更多利益交換與陰暗合作,這恰恰構(gòu)成了其人本質(zhì)又一次的暴露:想要獲得全新的開始與美好的生活,脫離碼頭爆炸案作為黑暗極致時(shí)刻的“底層人”身份,實(shí)際上卻是在“階層”上的努力,努力讓自己成為“上層人”,在現(xiàn)實(shí)里的結(jié)果只能是對(duì)拐賣主犯的上層人的靠近,隨之帶來了“表面掙脫與實(shí)質(zhì)歸依”之命運(yùn)。肖央對(duì)犯罪的深度參與、從被動(dòng)到逐漸主動(dòng)的犯罪過程,都能給出具體的表現(xiàn),并與當(dāng)下部分中的“受制于上層人”相結(jié)合,意味著其富商不過是上層人之表,內(nèi)里始終停留在“被上層迫害與利用、被迫犯罪的底層人”悲劇之中。
對(duì)于影片的構(gòu)建而言,這些內(nèi)容其實(shí)是更重要的部分。它對(duì)“少年與兒童”的傷害更加嚴(yán)重,并非單純的“導(dǎo)致其死亡”這一結(jié)局狀態(tài),而是在其生存有意識(shí)之時(shí)的罪惡折磨、犯罪同化,更加持續(xù),也是肖央在童年經(jīng)受的東西,由此引發(fā)了他的沉淪罪惡之命運(yùn),引出了靠后過往時(shí)段中的愈發(fā)沉淪。從兒童身外、籠罩其生活的“拐賣犯罪系統(tǒng)”(達(dá)蒙打造的官員參與機(jī)制),到兒童切身的貧民窟日常,再到肖央的逐步墮落、被社會(huì)/命運(yùn)愈發(fā)同化/馴服,都能有力地強(qiáng)化批判現(xiàn)實(shí)、命運(yùn)難抗的主題,卻因?yàn)槌叨葐栴}而被繞開了。因此,它的事件完全是模糊的狀態(tài),我們只得到了“每個(gè)人都是何定位與參與身份”的大致信息而已,而女綁匪等人的計(jì)劃也與之相關(guān),因此顯得非常草率,用粗梳的方式完成了一切。
影片的戲劇內(nèi)容極度單薄,只是以暴力與場(chǎng)景氛圍支撐著“罪惡命運(yùn)”感而已。并且,它也不能真的讓人物陷入從“由好變壞”的徹底黑暗之中,且要給予社會(huì)面的希望。佟麗婭等人的反轉(zhuǎn)完全抹除了曾經(jīng)的“被迫犯罪性”,這兩個(gè)人物是片中“正確價(jià)值觀”的關(guān)鍵,是純潔希望的符號(hào),分別對(duì)應(yīng)警察與媒體,也帶來了親情氛圍與正義必勝,而段奕宏的死亡、佟麗婭的“涉黑”,只是“全員墮落”在兩個(gè)希望符號(hào)上的暫時(shí)黑化而已。他們引出的“反轉(zhuǎn)”也同樣如此,反轉(zhuǎn)可以盡量避免對(duì)詳細(xì)內(nèi)容的正面表現(xiàn),只是用反轉(zhuǎn)的快速剪輯來帶過一切。處理過往真相時(shí),它采取了肖央與沙蒙敘述時(shí)的快速閃回,同樣是此目的。并且,這種方式也不需要給出暴力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執(zhí)行正義、假裝暴力與犯罪的“光明”部分,以此削弱了真正的尺度內(nèi)容,將大尺度停留在了噱頭的程度。
但是,佟麗婭與段奕宏的光明符號(hào)仍存,也就意味著影片主題的力度大打折扣。事實(shí)上,它理應(yīng)帶入更多的事件與時(shí)間點(diǎn),肖央在童年如何感染于犯罪的折磨而同化,長大后如何更積極地與達(dá)蒙合作致富,都是主題內(nèi)容的豐富來源,卻完全缺失了。它只能用段奕宏的死亡來削弱“正義希望”的完美性,隨后再給出一個(gè)盡量挽救彌補(bǔ)的最終收尾。
顯然,“光明結(jié)局”只是它的不得已而為之,因此顯得非常勉強(qiáng),真正想要觸碰的表意還在后面,以一種較為模糊的不確切方式出現(xiàn)。佟麗婭放過了肖央,肖央即將歸于司法系統(tǒng)的制裁,而下一代希望的女兒則與佟麗婭一起生活,免于犯罪的兒童環(huán)境,公眾更是得到了真相。但是,肖央同伙的車被一群孩子放入了炸彈,達(dá)蒙在監(jiān)獄中被滅口,兩處都以“火車/風(fēng)扇遮擋”的構(gòu)圖作為呈現(xiàn),暗示著日常表面的“正義必勝”遮掩下的邪惡仍存。孩子也再次參與了不知名者主導(dǎo)的罪行,拿錢后不知情地安裝炸彈,并在手忙腳亂中按下按鈕,其無意的姿態(tài)象征了“命運(yùn)的主導(dǎo)”,而非主觀有意,來源卻是不知名的上層者,是現(xiàn)實(shí)里的邪神。女兒同樣如此,她見證了肖央被滅口的時(shí)刻,由此陷入了犯罪環(huán)境,此后的人生必然與女綁匪和佟麗婭等人一樣,為了復(fù)仇而活。
純潔的下一代符號(hào)被玷污,上一代的佟麗婭與段奕宏同樣如此,他們的努力成為了無果的失敗,也在無意間成為了被動(dòng)的“罪惡者”:一切的結(jié)果似乎是送肖央接受司法制裁,實(shí)際上卻是送他被滅口,成為了助長上層者的幫兇。這種正邪之間的平衡,在影片的前中段是必要的,意味著底層人的“被迫犯罪,無法脫離”,其無意過被動(dòng)的犯罪加劇是命運(yùn)使然,也是上層者的控制引導(dǎo),但最終應(yīng)該變成徹底的罪惡,以此強(qiáng)化命運(yùn)感與相應(yīng)的批判性。
但是,成片的結(jié)尾表意卻依然停在了曖昧的“無意間犯罪”程度而已。對(duì)肖央的處理也是如此,他事實(shí)上只是無意間的殺人,失手憋死了兒童們,以此起始點(diǎn)奠定了此后一切罪惡的性質(zhì)。這并非不可行,在結(jié)尾處才被“反轉(zhuǎn)”揭示,卻淡化了他的墮落結(jié)果的程度,反而是與女兒綁架案的反轉(zhuǎn)同樣功能的“淡化黑暗尺度”。在這個(gè)階段中,所有場(chǎng)景都下起了陰雨,這是對(duì)開頭部分中“肖央下河求佛教洗脫”的再現(xiàn),同樣是水,卻是灰暗天空中的地獄之雨,是肖央在彼時(shí)的河中“洗脫失敗”的極端化形式,將所有人都籠罩在了被上層者擊敗、滅口的失敗命運(yùn)之中,甚至就是最確切無比的“碼頭爆炸案之地”,水正是碼頭,而開頭的“下河”則是爆炸案發(fā)生后的“尸體沉入河中”。他們并沒有戰(zhàn)勝真正的上層者、比佛教神明更有力量的社會(huì)特權(quán)階級(jí),水帶來的已經(jīng)不再是“洗清”,無論其成敗,反而變成了人間地獄的營造來源,以及對(duì)所有人被擊垮、歸于悲劇命運(yùn)的見證。這個(gè)概念式的表意是有效的,卻沒有戲劇層面的同量級(jí)支撐,不免讓人可惜。
在結(jié)尾,肖央死于槍殺,模糊身影的槍手意味著上層者的非個(gè)體存在,是“階層群體”的凝聚,在仰拍鏡頭中居高臨下,而前景里的槍口則是其階層的“命運(yùn)宣判”。“這是命運(yùn)”的最后臺(tái)詞,讓上層階級(jí)成為了最為確切的現(xiàn)實(shí)邪神,超越了此間段落的司法系統(tǒng)(警察局)與圍攏的民間公眾,更超越了肖央一直在拜而又始終無效的佛陀。而它的模糊,與足以殺死沙蒙的權(quán)力,也讓它成為了真正的邪惡來源,更高層的絕對(duì)存在,達(dá)蒙也相應(yīng)地變成了肖央等人一般的“下層被動(dòng)犯罪者”,而模糊身影與身份未知,也讓段奕宏與佟麗婭的計(jì)劃之失敗再次得到了體現(xiàn),他們沒能改變什么,也沒能觸及到真相,正義執(zhí)行更是失敗的。這反轉(zhuǎn)了曾經(jīng)的“反轉(zhuǎn)”,后者帶來的“抹除深度罪惡,正確價(jià)值觀樹立”被反轉(zhuǎn)掉了。“誤殺”的“誤”,也得到了多層次的落實(shí),先是對(duì)“受害人無罪”的誤判,隨后是第一次反轉(zhuǎn)中對(duì)“世界無希望”的誤判,最后則是再次反轉(zhuǎn)中“對(duì)第二次誤判之糾偏”誤判。
從劇情而言,這種開放式的結(jié)尾,又一次且“不給答案”的反轉(zhuǎn),無疑是一種爛尾,但也確實(shí)帶來了主題表達(dá)的正面效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影片在落點(diǎn)階段的巨大缺陷。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在短時(shí)間內(nèi)極其迅速的兩次反轉(zhuǎn),第一次用回溯的方式快速帶過肖央女兒綁架事件的真相,已經(jīng)讓段奕宏等人的正義計(jì)劃顯得無比粗糙,對(duì)綁架事件的“大尺度+深度黑暗”之表面的“反轉(zhuǎn)推翻”不夠扎實(shí),劇情也由此顯得格外薄弱,連同反轉(zhuǎn)之外的部分--達(dá)蒙引領(lǐng)的官場(chǎng)犯罪生態(tài),對(duì)兒童們的欺壓與拐賣“一線慘狀”,奠定、影響肖央“犯罪”心境與人生命運(yùn)的童年,肖央等人對(duì)兒童拐賣的參與,各家長們的痛苦---的同樣單薄狀態(tài),讓本片的戲劇部分愈發(fā)無可救藥。
我們當(dāng)然可以理解主創(chuàng),小心地防止自己觸碰到敏感內(nèi)容,干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事。但在這個(gè)不夠好的敘事基礎(chǔ)之上,片尾處的再次“二度反轉(zhuǎn)”,又在如此簡陋的劇情上又增加了一層DEBUFF:作為欺壓者的沙蒙犯罪生態(tài),被欺壓者的肖央等人的生活經(jīng)歷,都沒有具體的呈現(xiàn),而作為“達(dá)蒙之上的更高者”、將犯罪生態(tài)系統(tǒng)再擴(kuò)展的隱形上層人,以及其對(duì)肖央和佟麗婭等人的徹底戰(zhàn)勝,就都沒有根基可言了。
如果欺壓者與被欺壓者共同組成的“既有環(huán)境”是扎實(shí)的,那么模糊個(gè)體化的“群體”象征在結(jié)尾出現(xiàn),并將所有被欺壓者都打回到其環(huán)境之中,強(qiáng)調(diào)其“不可掙脫”與罪惡源頭的“某一(上層)群體”,是可行的方案,丹麥電影《狩獵》正是如此的收尾方式。但是,本片卻顯然沒有給出相應(yīng)的既有環(huán)境之基礎(chǔ),最后的二度反轉(zhuǎn)也就顯得生硬無比,因?yàn)槠洵h(huán)境如何讓人不可脫離的表現(xiàn)是單薄的,而再度強(qiáng)化的“不可脫離程度”也就同樣缺少了來源。在短時(shí)間內(nèi)的兩次反轉(zhuǎn),也嚴(yán)重削弱了第一次反轉(zhuǎn)“復(fù)仇計(jì)劃真相”的戲份空間,倒逼著這個(gè)部分的敘事愈發(fā)依賴快速剪輯與回溯倒敘,而閃回的內(nèi)容也愈發(fā)地被限制了長度,要將“壓縮”放在最優(yōu)先的位置,而這顯然是其最需要的“詳實(shí)有說服力”的反面。最終,二度反轉(zhuǎn)可能只會(huì)帶來“看內(nèi)容人”的不以為然,以及“多次反轉(zhuǎn)”的宣發(fā)標(biāo)語而已。
但是,在院線電影制約的情況下,這大概也就是唯一能拿出來的程度了。事實(shí)上,它對(duì)“反轉(zhuǎn)”的使用,在保證審查安全范疇內(nèi)盡可能提高的“尖銳批判”,在平衡之間的小心拿捏,都體現(xiàn)出了一種精明感。既不會(huì)被問責(zé),又想要“態(tài)度”得到的夸贊,既不想真的放下一切原有落點(diǎn)地去“完全光明”,又要讓自己處在“看上去光明”的表面之中,或至少給到足以過審程度的“光明分量”。它在表達(dá)邏輯上要符合前者,再將前者作為后者的某種加成手段,同時(shí)又要安放在“反轉(zhuǎn)”與“大尺度”這種利于短視頻宣傳、吸引眼球、強(qiáng)烈奇情的敘事模式元素之上。從這個(gè)角度上看,它無疑是一部標(biāo)準(zhǔn)的陳思誠電影。
只是,這一切都必須以戲劇完整性、主題完成度的巨大讓步作為代價(jià)。而“實(shí)際上并不在意主題與內(nèi)容,只是將之作為一種包裝”這一點(diǎn),也恰恰是陳思誠的最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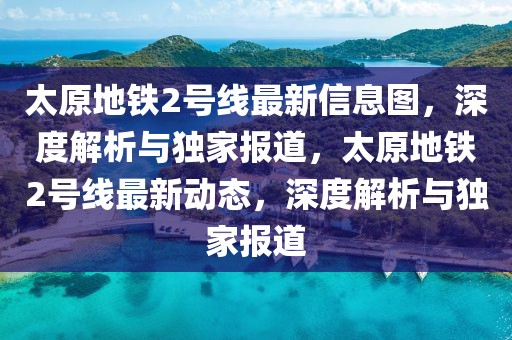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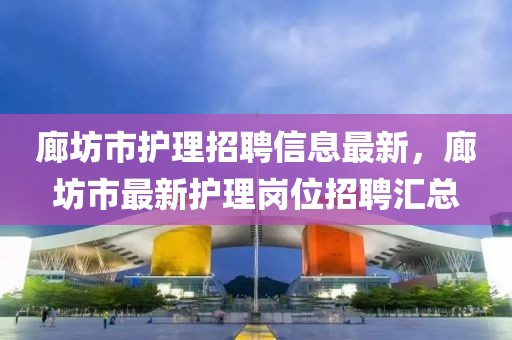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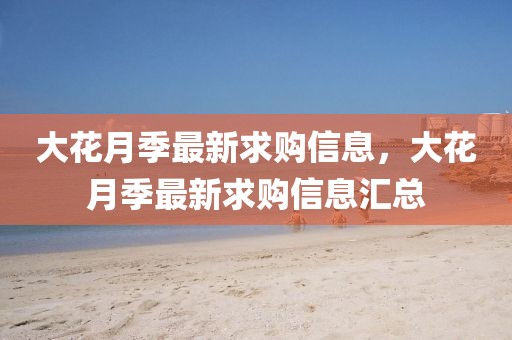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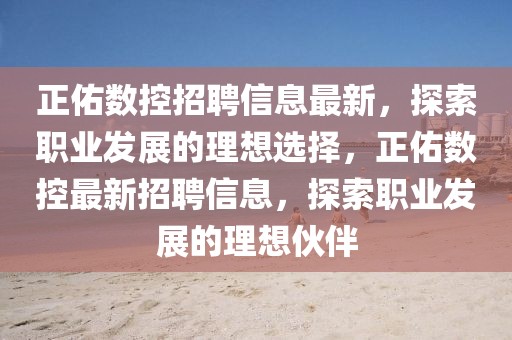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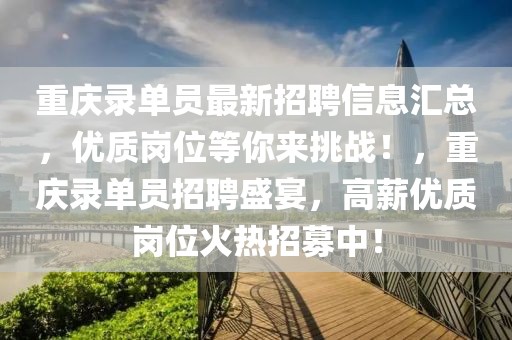
 魯ICP備2020050029號(hào)-1
魯ICP備2020050029號(hào)-1 魯ICP備2020050029號(hào)-1
魯ICP備2020050029號(hào)-1